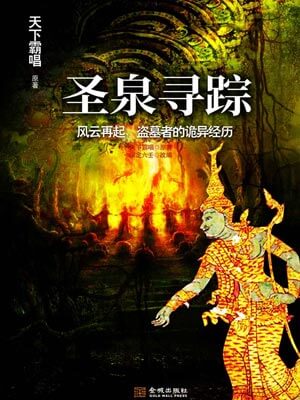天亮之前,秦北洋、阿幽还有九色,悄悄爬下屋顶。冬天快到了,6点钟天还是黑的,他们躲过巡捕房的层层搜捕,无声无息地摸到了提篮桥。遥望坚不可摧的远东第一监狱,秦北洋感到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又在心里默默为齐远山祈祷,但愿他不要被抓进去。
6点钟,他敲响了精武体育会隔壁的一扇房门。他不担心自己被人看到,但怕火红鬃毛的九色被人注意。
开门的是陈公哲,练家子惯于早起,已是一身练功的短打。这里是他的私宅,包括体育会的占地,也是他捐献的。
秦北洋带着女孩和大狗抢进门里,跪下说:“陈先生,偌大的上海,我再无第二个可以信任之人,请救我们一命。”
陈公哲锁好大门,将他们迎入楼上书房,小心地把窗帘拉好,确认没有被人发现。随后,秦北洋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
甫一听完,陈公哲面色凝重:“虹口巡捕房的大屠杀案,我也早有耳闻,也担心我们精武体育会的学员,会不会被卷入到这一事件。没想到,你和齐远山又成了海上达摩山灭门案的嫌疑犯,此事真的太棘手了。”
“陈先生,我给您添麻烦了,我和阿幽这就出去,再找地方落脚吧。”
“这算什么话?”陈公哲一把将他按下去,貌似文弱书生,但手上力道惊人,“在苏州虎丘初次见面,我就觉得你不是普通人。虹口柔道馆一役,加上我们在外白渡桥交手,秦北洋,我相信你是无辜的!不想看到你蒙受不白之冤,落到巡捕房或恶人之手。”
陈公哲端来热腾腾的早饭,还给九色带了几块肉骨头。但它嫌弃地躲开。秦北洋只能解释:“这不是狗,它不吃肉,也不吃草,它只以……空气中的微生物为食。”
“天下之大,必有怪异之物。等到下世纪,科学终将给个说法。”
陈公哲在二楼腾出间客房,保险起见,他关照秦北洋不要下楼,务必拉紧窗帘。
客房不大,只有一张床。秦北洋让阿幽睡床上,自己打地铺,九色根本不用睡觉,直接变成青铜的幼麒麟镇墓兽。
烦躁地过了整个白天,隔壁的精武体育会里不断传来练功的吆喝声。他郁郁寡欢地隔着窗帘眺望天空,不晓得齐远山有没有脱离险境?阿幽也没怎么说话,偶尔咿咿呀呀唱几段绍兴戏,都是才子佳人的故事,秦北洋言不由衷地给她鼓掌,又要她声音轻点。
这天晚上,陈公哲家里来了个客人。
秦北洋不敢下楼,客厅位于正下方,通过地板缝隙,可以看到客人过早谢顶的脑袋——年约三十,中等个子,眉宇间有英雄气,嘴角微微上翘。陈公哲跟他关系不错,可以互相拍肩膀的那种。
“凯申兄,好久不见,你刚从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归来?”
“今晚登门拜访,我谨代表孙中山先生捎句话——先生答应担任精武体育会名誉会长,亲笔题写‘尚武精神’匾额,不日将从广州运到上海。”
客人操着宁波乡下口音,幸好上海话与宁波话大半相同,楼板之隔的秦北洋不难听懂。
“啊!此乃大喜事也!”
“不必客气!”客人面露倦容,频频向窗外探望,“呃,你知道,我也是青帮成员,昨晚出了一桩大事,可谓数十年不遇。”
“你是说……欧阳思聪?”
“对,想必公哲贤弟也有耳闻,堂堂的青帮头面人物,居然惨遭灭门,被刺客割喉,搬空了家中的财宝,又纵火焚烧,奇耻大辱!一言难尽。”
“凯申兄可否知道内情?”
“我一整天就跟青帮商量这个事情呢!昨晚,海上达摩山的大火,起得快,灭得也快。巡捕房与消防队都只隔了两条街。连同欧阳思聪在内,总共十四条人命!大部分尸体还能辨认,全部死于一刀割喉。明摆着,凶手与两个多月前的虹口巡捕房大屠杀的凶手是同一批人。”
“对了,你说总共十四条人命,其中可否有欧阳思聪之女,安娜小姐?”
陈公哲的这句话,其实是代替楼上的秦北洋问的。
“青帮已经查过了,凶案发生的当天早上,安娜小姐已经坐船回了老家。”
“老家是在?”
“达摩山。”
“原来,海上达摩山之名是因此而得来的。”陈公哲爱好广泛,其中也有文物考古一项,海上达摩山作为沪上第一家私人博物馆,在圈内名闻遐迩,“我知道,达摩山,乃是东海上的一座孤岛,并无任何轮班通航,安娜小姐必是专门雇了一艘船只登岛。”
“听说岛上连电报都不通,估计此刻,安娜小姐尚不知父亲惨死。”
帮秦北洋打探到这消息,陈公哲也算完成任务,他又转回正题:“凶案可有嫌疑人吗?”
“一个叫齐远山,一个叫秦北洋!”
客人冷静地说出这两个名字,正在楼上偷看的秦北洋,心脏几乎要绷断,自己果然被栽赃成了杀人狂魔。
“巡捕房已经发布通缉令,悬赏还是一万英镑。青帮悬赏的是这两个人的脑袋,赏金各一万大洋。”
“真是闻所未闻!”
陈公哲故意把声音说得很响,要让楼上的秦北洋听到。
“最近上海的这两桩凶案,虹口巡捕房连巡捕带犯人死了十五个,海上达摩山又死了十四个,也是闻所未闻啊!齐云山、秦北洋,这两个凶犯,前者是欧阳思聪的关门徒弟,后者是欧阳家的私家工匠,犯下了欺师灭祖、背叛师门的十恶不赦的大罪!按照青帮的老规矩,是要抽筋剥皮下油锅乃至于诛杀全家的。现在全上海已炸开锅了,每个街头巷尾,都有印度巡捕和青帮兄弟在搜捕这两个人。”
陈公哲只管听,却没有搭话,客人话锋一转:“公哲贤弟,我听说这两个凶犯,也是你们精武体育会的学员。其中那个秦北洋,前些日子踢了日本人的虹口柔道馆,你们还为他摆了庆功宴。”
“嗯……我承认。”
“你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吗?”客人盯着陈公哲严肃的双眼,忽然一笑,“哈哈,公哲贤弟,我是开玩笑的。你真把我当作青帮的门徒了吗?青帮之身份,只为革命便利,同盟会时代至今的历次起义,我们不都是如此吗?”
“对!对!帮会就是一把刀,革命就要是踩着这把刀往上走。”陈公哲还是把话题扯了回来,“再说说看,秦北洋和齐远山,他俩不过是十七岁的小孩子,如何有胆量犯下那么大的事儿呢?”
“听说,他俩的年纪虽小,却都身怀绝技,既擅长射击,又会刀枪等冷兵器,还在你们这里练过武术,杀人对他们而言并不难。还有青帮兄弟说,曾亲眼看到秦北洋使用匕首,瞬间割断一匹马的喉咙,这也让巡捕房联想到刺客的动作。”
趴在地板缝隙偷听的秦北洋,知道这事倒不是栽赃——欧阳家养着一辆马车,有次发生翻车事故,马的脊椎骨摔断生不如死,秦北洋出于仁慈,迅速割喉结束马的痛苦。
楼下的客人接着说:“巡捕房已列出这二人的杀人动机——贪图海上达摩山的宝贝。三个多月前,欧阳家发生过一起盗窃案,当时被捕的盗墓贼,根本就是齐、秦二人的同伙,原本要里应外合偷盗宝物,结果被欧阳思聪的女儿发现。他们演了一出苦肉计,让盗墓贼被抓进巡捕房,而让秦北洋留在欧阳家。齐远山又获得欧阳思聪信任,成为青帮老大的关门弟子。又隔一个月,刺客制造虹口捕房惨案,救出了被羁押的盗墓贼。”
“证据呢?听来都是猜测和推断。”
“火烧达摩山时,许多人亲眼看见齐远山、秦北洋逃出宅邸,身上还沾染受害者血迹。案发前两天,欧阳思聪派遣齐、秦二人去处理一桩绑架案。昨晚,这二人悄悄潜回上海,伙同其他刺客,杀死欧阳家里所有人,又搬走价值连城的古董,最后纵火焚烧。”
陈公哲半天都不言语,语气低沉道:“可惜啊可惜,犯下欺师灭祖罪行的秦北洋与齐远山,必死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