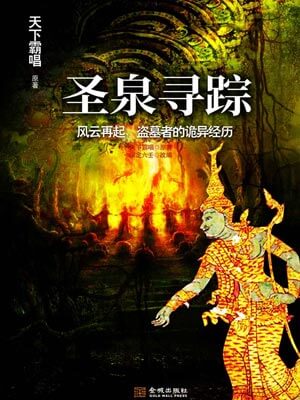古时候,要想去见一个人,你就背上行囊动身。哪怕走好几夜的路,爬好几座的山,渡好几条的河,到他面前说上几句短短的话,一起躺在稻田,仰天看星星。然后执手道别,再渡过好几条的河,爬过好几座的山,走好几夜的路。卸下行囊,独自倒在稻田,仰天看星星。做个梦,慢慢地想他,直到死。
达摩山。
东海、落日、晚霞,犹如刚铸造完工的青铜器,沿着海平线飞奔而来,洒在“赛先生号”的纺锤形艇身表面,将天圆地方的铜钱纹染成金币。
飞艇悬浮在海岛上空,秦北洋率先钻出吊舱,爬下垂落的软梯。当他的双脚跳落地面,俯瞰达摩山怪石嶙峋的海面,却见到一个穿着西洋女学生服的姑娘。
她的双手提着裙摆奔跑,宽边帽子被狂风吹走,像个金色小光点旋转飞向落日,自来卷的黑发四散飞扬。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安娜!”
秦北洋在搂住她前,却又后退半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这才意识到,自己是来给她报丧的。
欧阳安娜的拳头捶着他的胸口,胡言乱语了一大堆,眼眸里转着泪珠,最后问一句:“秦北洋!是我爹派你来接我回去的吗?”
“你爹……”
话音未落,吊舱下的软梯又爬下一个男人,穿长衫的叶克难口噙礼帽。阿幽紧跟着下来,叶克难托着她在地面站稳。
秦北洋不敢回答安娜的问题,仰望悬空的飞艇:“九色咋办?”
吊舱里探出一只幼兽的脑袋,接着是它大半个身体。
阿幽大喊一声:“不要跳啊!”
海面反射夕阳的波光,让九色变得五彩缤纷,刺得所有人睁不开眼。
唯有秦北洋,他看到一只飞翔的兽,在大海与天空之间,划出一道彩虹般的弧线。
九色落到地面上,小狗似的打了个滚儿,摇摇脑袋和尾巴,居然毫发无损。
欧阳安娜抢在秦北洋之前,抱住九色,亲着它的赤色鬃毛,像久别重逢的老友。
而在他们的头顶,美国技师探出吊舱来挥手作别。飞艇无法在岛上停留,必须原路返回上海。天圆地方的铜钱纹升上天空,重新转动螺旋桨,向着落日的方向飞去。
秦北洋摸着九色,目送“赛先生号”融化在残阳如血的海平线上。
“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吗?”
安娜乖巧地向叶克难与阿幽打招呼。
秦北洋先介绍了叶克难,京城名侦探的派头,无论大姑娘小媳妇碰到都五体投地。阿幽怯生生地作答,还想要缩到别人身后,倒是安娜抓起她的手:“好漂亮的小妹妹!”
天黑了,欧阳安娜带着他们上山,来到灯塔下的石头大屋。虽是海上达摩山的小姐,但毕竟是在海岛出生,点上薪柴打开油锅,阿幽也来帮忙,两个姑娘做了一顿海上晚餐。
在飞艇上度过大半天,秦北洋已饥肠辘辘,吃了好多螃蟹、海带子、八爪鱼和淡菜,都是以前从没吃过的食材。就连京城名侦探叶克难,也连连夸奖这岛上的海鲜美食。
酒足饭饱,欧阳安娜又提了那个问题:“我爹还好吗?他命令我回到岛上的那一天,我很担心他。”
秦北洋还是支支吾吾,倒是叶克难大方地说出真相:“安娜小姐,欧阳先生已不在人世了。”
出乎意料,欧阳安娜只沉默了片刻,眼眶中有泪水打转,却未曾掉下来,反而镇定自若地回答:“被我猜中了!他早已预感要出大事,只是不知哪一天降临。他把我送到这孤岛上,就是要我躲过这场灾祸。我爹说过,男人可以死,但不可以逃。他宁愿留在家里,等那些人到来。而他明白,女儿安娜,只要活在这世上,必将为父报仇。”
叶克难不禁赞叹:“欧阳思聪有你这样的女儿,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安娜,现在我和齐远山成了杀死你爹的嫌疑人,整个上海贴满有我照片的悬赏通缉令。”秦北洋索性和盘托出,让她自己来决定吧,“但阿幽可以为我证明……”
“不必解释!”她堵住秦北洋的嘴巴,“你若有罪,也不会和叶探长一起来到这里。”
“秦北洋这次上岛来,一是来向你报丧,二是躲避上海的通缉,三是想让你为他证明清白。”叶克难代替他说了,“我是京城的探员,在上海租界无司法管辖权。但这座岛是中华民国直接管辖的领土,我奉内务总长之名探案捕盗,可以调查欧阳思聪的案件。”
“今晚,你们若不嫌弃,就请住这间石头房子。”欧阳安娜回头对阿幽说,“妹妹,你跟我睡一间屋吧。”
自然,秦北洋跟叶克难睡一屋,九色蜷缩在他的脚头。欧阳家的老屋年久失修,除了安娜的卧房,其他都破烂不堪,四面通风。两个男人一头幼兽,挤在一顶大蚊帐里,抵足而眠。
秦北洋是北人,也在皇陵地宫住过,更见识过太行山上的暴风雪,今夜住在这东海孤岛上,却被冻得满脸鼻涕。南方的寒冷,深入骨髓,宛如刀割针刺,让人无所遁形。没有炭盆,更没有火炕,只能依靠体温驱散寒冷。叶克难也冻得发抖,幸好九色发光发热,让京城名侦探为之称奇。
第一次跟镇墓兽睡在一起,秦北洋感觉回到地宫,变成棺椁中的帝王,不禁哑然失笑。又想起半年前,在太行山中的袁世凯陵墓,他收养的那头小狼,最终命丧辫子军的刺刀之下。这回他发誓,再也不能离开小伙伴,无论是小狼还是小镇墓兽。
睡不着,秦北洋悄悄下了床,九色立刻抬头。他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让九色留在床上,没有它的热量,叶克难怕是要被冻死了。
走出石头大屋,来到子夜山顶。他在灯塔基座下绕了一圈,发现有个小门,踏上螺旋形的楼梯,直通顶层。
灯塔之巅,会当凌绝顶,强光几乎刺瞎眼睛,电流发出嗡嗡的声音,盖过山顶上的狂风。
有人尖叫一声,秦北洋的裤裆挨了一脚。原来是欧阳安娜。
虚惊一场,等到旋转的灯光再照过来,她才看清楚秦北洋的脸。
“对不起,我想起了爹,辗转难眠,就上来看星星。”欧阳安娜脚下还有一堆灰烬,原来在给父亲烧纸钱呢,“呃,我是天主教徒,本不应该做这种事。但我爹不是啊,所以按他的习惯来。”
“等我洗刷罪名,我就在岛上给你爹找个龙穴,亲手给他做个气派的坟墓!”
秦北洋又说出了老本行,他捂着疼痛的下半身起来。安娜沉默着站到大灯侧面,避开刺眼的光。透镜放射可达二十海里,四面八方旋转,警告轮船避开这座岛周围的暗礁。秦北洋脱下外套披在她背上。黑色大海,茫茫虚空,中国大陆、日本列岛还有朝鲜半岛,似都遥遥在望。
“建造这座灯塔的工程师是个德国人,也是业余天文爱好者,他意外发现,达摩山是极佳的流星观测点。”
“德国人?”秦北洋想起自己还记得的德语单词,又望向星空,“除了流星,我还想看到彗星袭月。”
东海中央的孤岛上,仿佛回到一千五百年前,达摩祖师登陆的年代。灯塔的光,扫过北半球灿烂的星空,飘浮在整个银河系。
“太漂亮了!如果,我现在就跳下去的话,会不会解脱这辈子所有的烦恼?”
背着光,看不清彼此眼神,秦北洋淡淡地说:“不会的,你会把烦恼带去下辈子。”
“我的祖先把房子造在山顶上,离群索居,多不方便啊!但是,因为他们遭到了岛民们的歧视,被迫搬到这个地方,好像这样就能离人间远一点,离星星更近一点。”
“离星星更近一点!”
秦北洋在她背后发出浓重的呼吸,热气喷到她后脖子。安娜一转头,琉璃色的眼珠子,在黑夜里熠熠闪光,如同天上的某颗星星:“对了,你是什么星座啊?”
“我不知道啊,我是在庚子年的十月初二生的,阳历11月23日,当日节气小雪。”
“那你是射手座!又叫人马座,黄道十二宫之第九宫。但11月23日是天蝎和射手的交界,你同时具备这两个星座的特点——天蝎深沉、严肃、神秘,外冷内热;射手天生热爱冒险,酷爱自由。你们鄙视中庸,要么贵不可言,要么一贫如洗。”
“好吧,我现在就是一贫如洗!至于冒险和自由嘛……我出生在唐朝古墓的棺椁上,生下来就没了亲娘,九岁又死了养父母,被送到清朝皇陵的地宫里,这算不算冒险?”
“你的一生将注定颠沛流离,身犯险境!”在上海法租界的教会学校,安娜可是个神婆,许多同学都来找她算命,她盯着秦北洋的眼睛,“天蝎与射手交界的人啊,关心整个世界,胸怀宇宙,更像个革命家!而且,你会很有女人缘,这辈子会有很多个女人!我不喜欢!”
“怎么会呢?你说的好像不是我欸,西洋人的星座一点都不准呢。”
安娜伸手按了按他的鼻子:“因为啊,我跟你是一样的星座,也是天蝎射手交界,所以最准了呢!对了,你想知道欧阳家的过去吗?”
“一直很好奇呢!”
“欧阳家本是广东人,我的曾祖父,跟随天王洪秀全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天京陷落,我的爷爷还是个少年,他被清廷流放到孤岛上。”
“原来你是太平天国忠良之后。”
“另一种说法是‘长毛贼’!我爹是欧阳家在达摩山的第二代,他有个双胞胎姐姐,名叫欧阳思凡,人称‘魔女’。她的故事说起来可就长了……我爹年轻时,出海到南洋,在爪哇岛认识了我妈,她是日惹苏丹国的混血族人。”
“怪不得,你长得不同于一般的汉人,因为你有南洋异族的血统。”
“人们都说我的眼睛奇怪,既不像洋人,也不像中国人,谁能想到来自南洋呢?我在达摩山上出生。那些年,我爹天天等在悬崖上,发现有船只触礁遇难,就驾着小舟前去打劫。不分中外,一律杀死幸存者,夺取金银财宝。他常到上海销赃,因此加入青帮。民国元年,我妈病死在岛上。我被爹接到上海,在教会学校读书。天天听老师说《圣经》故事,我就接受了洗礼。虽然,我爹还是异教徒,但也没反对,他说这样更好跟外国人打交道。他在虹口造起海上达摩山,为了纪念欧阳家族的故乡,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是从哪里来的。”
“原来,叶探长想要调查的海盗,就是你们家啊!”
“他是不是跟你说——从中国运庚子赔款到日本的轮船,遭遇海难沉没,雪花花的白银,就埋藏在达摩山上?”
“庚子赔款!”提到自己出生的庚子年,秦北洋便觉是奇耻大辱,“那你知道多少?”
“父亲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但我想,这些白银原本就不在他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