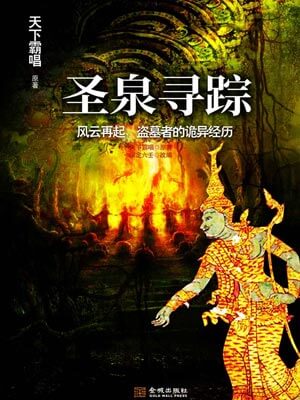刚过去的这一夜,农历七月半的鬼节,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最悲伤的一夜。
整整十年前,1907年9月2日,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件?
上午8点,惨遭灭门的虹口捕房的屋顶上,公共租界巡捕房希尔顿警长、欧阳思聪、秦北洋、齐远山,已牵扯到十年前的往事。
欧阳思聪摇摇头:“那时候,我还没到上海来呢。”
“但我在上海!二十年前,我就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工作了。在我的印象里,那年9月,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包括华界,都没有发生过大案子。我查过巡捕房的档案记录,9月2日只有些不值一提的小偷小摸被捕。”警长咬着烟斗说,“但是,陆地上太平无事,不代表海洋上也风平浪静。”
“海洋?”
警长盯着欧阳思聪的眼睛:“1907年9月2日,有一艘日本羽田汽船公司的客轮,排水量两千吨的徐福丸,开出上海港向神户驶去,却在东海上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对……你提醒我了,这事儿我也听说过。”
秦北洋发现,欧阳思聪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这艘轮船,载运着四百多名乘客,包括羽田商社的社长,他叫……”警长翻开小本子,“对,羽田龙马。船上还有日本政府委托运输的一笔巨款,也是中国交付给日本的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
一提到庚子年,秦北洋就莫名地发抖,何况是压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庚子赔款。
“Boxer Indemnity!我们西方人管它叫拳乱赔款。中国政府至今每年都要缴纳给列强。而在1907年,中国缴给日本的赔款大约是一百万两白银,全都装在羽田汽船的徐福丸上。9月2日,清晨7点,轮船航行出吴淞口。到了这天晚上,就失去了无线电联系。羽田商社和日本政府派遣了很多船只去搜索,但都没有这艘船的消息。”
在一旁听着的秦北洋,想起八年前,天津徳租界灭门案发生的那一夜,养父仇德生说起过这桩大案——庚子赔款中的一笔百万白银,莫名其妙地在东海上失踪了。
“这个……”
“在中国东海之上,中国与日本航线的中心点上,有座孤岛叫达摩山——Bodhidharma Island。”警长又看了一眼笔记本,念出岛屿的英文名称,仿佛是一座印度或锡兰岛屿,“据我所知,达摩山附近的海域,除了暗礁密布,还有凶残的海盗出没。”
“好吧,我承认,达摩山是我的故乡。”
“1907年9月2日,欧阳先生,你在哪里?”
“达摩山。”
希尔顿警长咬着烟斗说:“百万白银的轮船失踪后,日本政府曾派遣海军陆战队登上达摩山扫荡,但并未发现白银的下落,连一个幸存者都没找到。”
“嗯,我也有所耳闻,不过那时我正好去宁波经商,所以没碰上日本鬼子。”只要提起日本人,欧阳思聪就是满脸不屑,“对不起,尊敬的警长先生。如果,你是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日期,就把无辜的我牵扯进这桩大案,我要向工部局提起抗议。难道说,你要指控我犯有海盗的罪行吗?”
“我不关心什么海盗罪行,东海达摩山并不在我的管辖范围。欧阳先生,你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公馆——海上达摩山,恰好在虹口巡捕房的管区内。而我只关心今天凌晨,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桩凶案,我们巡捕房有十位英勇的同袍壮烈殉职,我必须为他们复仇!”
面对愤怒的警长,欧阳思聪的两颊也在发抖。突然,他在秦北洋的背后推了一把。
“我们为何要舍近求远?为何不说说一个月前,闯入我家的盗贼呢?就是这位勇敢的少年,奋勇地以一敌四,将入侵的贼人们击退,生擒了盗墓贼小木。”
齐远山以为欧阳思聪要把秦北洋当作替罪羔羊,擦干净嘴边的呕吐物,挺身而出:“欧阳先生,我们也是刚到上海才三个月,根本不认识那些个强盗啊。”
“你真为兄弟讲义气!”欧阳思聪拍拍他俩的肩膀,“希尔顿警长,我想说,当时盗窃我家的四个盗匪,巡捕房只抓获了其中一个,还剩下三个盗匪。为何不是那三个人来劫持同伙的呢?”
“根据小木的口供记录,他说另外三个盗匪,跟他只是临时性的同伙关系,都是些有勇无谋的兵痞。当然,我也无法判断,这份口供的真假,也可能这个团伙,还犯下了其他十恶不赦的罪行。另外三个在逃的罪犯,必须要把小木救出来,或者灭口。”
“警长先生,可以让我说话吗?”
憋了半天,终于到了秦北洋爆发的时候。
没等警长点头,欧阳思聪先说话了:“可以,我带你过来,就是让你尽量多说的。”
“我知道血洗巡捕房的凶手是谁!”秦北洋深呼吸了一口气,“首先,肯定不是在海上达摩山逃走的三个盗窃犯,我跟他们几个人正面交手过,知道这些人几斤几两,绝无胆量跑到巡捕房来杀人。”
“说下去。”
希尔顿警长叼着烟斗,托着下巴,专注地看着这个十七岁的中国少年。
“八年前,宣统元年,天津德租界发生过一桩灭门案。有两个凶残的刺客,入侵一户普通居民家中。他们杀害了一对中年夫妇,又要谋害一个九岁男孩,幸亏被京城巡警局的探长所搭救。那次灭门案中,有两名巡捕被割喉身亡。男孩反抗之中,刺伤了其中一名年轻刺客,导致他的右脸多了一道扭曲的伤疤。”
秦北洋说到这里,又奔到小阁楼,向唯一的目击者求证:“喂,那个脸上有刀疤的杀手,你看清楚是在哪边脸上吗?”
幸存者想了想,手指在右侧脸颊比画一下,像条蜈蚣似的爬过,几乎延伸到耳边。
“就是他!几个月前,张勋复辟,北京发生过一桩大案。三个刺客闯入监狱,杀死包括典狱长在内的许多狱警。杀人手法就是匕首割喉。今天凌晨虹口巡捕房的惨案,与八年前天津德租界灭门案、今年北京监狱大屠杀,均属同一刺客团伙所为。”秦北洋的脑子飞转,所有情景就如镇墓兽图纸,一格格浮现眼前,都与自己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谁有纸笔?”
欧阳思聪和齐远山摸摸口袋都摇头,倒是希尔顿警长贡献出了笔记本……
秦北洋精确地几笔勾画,刺客的匕首已跃然纸上——长约三寸,锋利无比,带有血槽,象牙手柄,装饰有精美的螺钿图案。
彗星撞击月亮,画得惟妙惟肖,呼之欲出。
警长对他频频侧目:“你是我所见过最特别的中国男孩。八年前的灭门案,我也有所耳闻,当时正好路过天津,确实张贴有通缉犯的画像。几个月前,北京监狱大屠杀,更是传遍了整个远东地区的警界。”
“北京警察厅还有凶器实物,你们可以去调查,我绝无半点假话。”
希尔顿警长摘下烟斗,指着秦北洋问:“可是,孩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就是八年前灭门案中唯一的幸存者——差点被他们杀死的九岁男孩,也是我给那个年轻刺客的脸上留下了伤疤。我曾立下誓言,要亲手杀死那两个刺客,为父母亲报仇雪恨。现在,至少其中一个刺客,已经出现在上海。”
“北洋,他们为何要杀你全家?”
欧阳思聪问出这个重要的问题。
秦北洋不能说出镇墓兽与墓匠族的秘密,苦笑着摇头:“或许……我是天煞孤星!”
至此,这桩案子总算是有了重大进展,至少能串联起凶手的作案轨迹。
趁着警长转身记录,欧阳思聪贴着秦北洋耳边说:“谢谢你,替我解围了。”
“我只想抓到那些刺客!”
站在血案现场虹口巡捕房的屋顶,秦北洋转身面对外滩与黄浦江,浩浩荡荡的江水向吴淞口奔流而去。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如同迷宫般的蚁穴,藏着三百万蝼蚁般的人民。而那张刺客的脸,不知在哪个角落?
此时此刻,对面楼顶有一台照相机对准了他的脸。
照相机背后,有张刺客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