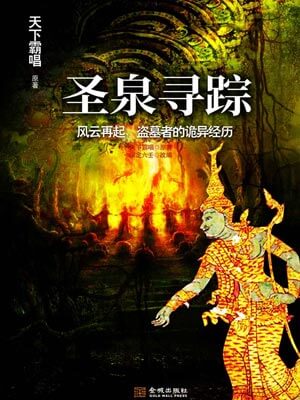“扑通……”
这下酒全醒了。泡在深秋冰冷的苏州河里,秦北洋吃了好几口水,幸好从小在海河里游泳,踩着水没沉下去。
苏州河两边都是水泥堤坝。齐远山则是旱鸭子,在桥边干瞪眼喊救命。当陈公哲准备脱衣服跳水救人时,一根竹竿伸到了苏州河心。
秦北洋抓紧竹竿,只见齐远山和陈公哲都在桥上,又是谁在救他?竹竿带他游到接近沙俄帝国领事馆水域,他才找到台阶爬上来,刚要向救命之人谢恩,地上徒留竹竿,不见人影。
齐远山与陈公哲绕过桥头跑来,秦北洋抹去脸上水藻和污垢,看着黑魆魆的街道:“救我的人为何逃跑了?有人在跟踪和偷窥我们!”
“嗯,要小心了。”
秦北洋成了狼狈的落汤鸡,连打十几个喷嚏,又大笑道:“陈先生,我本想试试你的武功,没想到你是深藏不露。”
“得罪!得罪!”陈公哲也忍俊不禁,“跟秦小弟一起玩耍,真是有趣得紧!”
秦北洋披上齐远山递来的毛巾,头顶散发白乎乎的热气,不知道的还以为内家大师在运用真气。
“陈先生,今日与倭寇的柔道馆比试武功,你要是亲自上阵啊,必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习武之人,本为强身健体,不可逞强好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出手!霍东阁对付那个日本人,也是绰绰有余,但作为霍元甲的传人,不动如山才是最好的选择。”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秦北洋又打了个喷嚏,长这么大,他还没崇拜过什么人。
三人在外白渡桥钢梁下别过。夜色下的黄浦江,一艘外国军舰鸣着汽笛开过,波浪在江堤上打出一片水花,几乎淹过外滩公园的地面……过了桥,离海上达摩山也不远了,秦北洋和齐远山跑步回去,抵消落水后的寒气。两人穿过两个路口,看到虹口巡捕房大案的悬赏通缉令。
夜深人静,秦北洋突发奇想,决定到案发现场转转。齐远山也拦不住,转过一个拐角,到了虹口巡捕房门口,那里果然贴着工部局的封条。巡捕房已在四川北路另觅新址办公,这栋楼据说不吉利,可能会被弃用。秦北洋在路口观察,对面有栋六层高楼,站在那个楼顶,可清晰地观察到巡捕房内的一切动静。
“远山啊,我们一起看过案发现场,我在想,两个刺客是怎么把凶器带入巡捕房的呢?”
秦北洋脑中浮现起印度巡捕的模样,都是身高体壮的大汉,北印度的锡克人与旁遮普人,平常对中国人颇为凶悍,凡是抓获疑犯首先会搜身,不可能让人把那么大的匕首带进来。
“必有内应!也许那些匕首,早就藏在巡捕房里了,只要刺客装作犯人被抓进去,就能抽出来杀人。而我们对面这栋楼,就是监视虹口巡捕房的最佳位置。”
齐远山摸着自己脖子。白天,若非秦北洋及时出手,他必会被日本柔道高手拧断颈椎,脖子至今酸痛,让他心有余悸。
“你还不赖啊!”秦北洋注视着街道东去的尽头,“这绝非两个刺客的屠杀,而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刺客只不过是最终杀人的子弹,扣动扳机的人又是谁呢?”
“你不是说过吗?跟海上达摩山的小镇墓兽有关系。”
“是,但以他们干净利落地屠杀巡捕的能力而言,要杀到欧阳家府邸也并非难事。所以,那天欧阳先生的面色非常糟糕,他知道作为青帮老大,也未必能保护自家安全。”
“如此说来,他们除了小镇墓兽,还有更重要的目标?”
“我?”
“北洋,你的脖子后面有两块胎记,跟幼麒麟镇墓兽的鹿角形状很像,只是你这个火红,它那个雪白。”齐远山继续用毛巾给他擦头发,“你的身上,也许还藏着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前几天,我们两个去卡德路的澡堂子洗澡,你说感觉有人偷看你,我还开玩笑说是有男人喜欢上你了。现在想来,必是有人在偷看你后脖子的胎记。”
秦北洋下意识地摸了摸后颈:“对,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坠入苏州河以后,还会有人用竹竿子来救我的原因,他们一直在盯着我。此时此刻,也许就在我们身后。”
“别吓唬我!”
齐远山警觉地回头看身后,竟然真的有个灰色人影,头戴礼帽,身着长衫,面孔隐藏在阴影中,如同屠杀了这栋房子里所有人的刺客。
“什么人?”
秦北洋暴喝一声,向那鬼魅般的人影扑去,对方轻巧躲开,四散蔓延开一阵杀气。
齐远山从另一个方向发动攻击:“小心他有匕首!”
空无一人的街头,路灯照出三个长长的人影……辗转腾挪,拳脚生风,犹如一部无声电影,全靠光影交错撑起画面。
对方同样好身手,只是迟迟没有亮出凶器,用胳膊拆挡了几招,眼看双拳难敌四手,就要被秦北洋与齐远山逼入死角。
突然,他的手中多了一把手枪,对准秦北洋的鼻子。
枪声没响,秦北洋却放下拳头:“你不是刺客!因为你用枪,而刺客只用匕首。”
“秦北洋,四个月不见,你又有长进了!”
声音分外耳熟,来人在路灯下露出脸庞。三十出头的男人,拧着一对浓密的眉毛和小胡子,目光如同刀子,却让秦北洋喜不自禁——北京警察厅的探长叶克难。
“叶探长!你怎么来上海了?”
叶克难收起手枪,摘下礼帽,微笑道:“来看黄浦江的风景不行吗?”
“请受秦北洋一拜!”
“请受齐远山一拜!”
两人要为四个月前,叶克难从张勋复辟的监狱中,将他们解救出来而谢恩。
“举手之劳,何足道哉!”
秦北洋抓着他的手说:“对啦,叶探长,你知道我爹在哪儿吗?”
“放心吧,他的伤势已经痊愈,现在北洋政府的南苑兵工厂任首席机械师。”
“我爹去兵工厂做机械师?”
“我也好久没见过他了,据说在为北洋军研制一种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秦北洋回头看了齐远山一眼,“莫非是镇墓兽?”
“那可是军事机密,国务总理下令,陆军次长亲自监督的。我一个刑侦查案的探长,哪能知道这些内幕。”
“只要他没事就好!做了首席机械师,至少饷银不会少,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听说他们最近去挖墓了。”
“挖墓?”
叶克难回头看着虹口捕房,言归正传:“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希尔顿警长,通过北洋政府内务部,邀请我来上海协助破案。内务总长担心这是政治案件,害怕引起英美列强干涉,吩咐我尽快破案。但我是北京警察厅的探长,只能给租界做顾问,无权参与抓人行动。”
“1907年9月2日。”秦北洋也不客气了,指着被贴封条的凶案现场,“这扇大门后面,凶手用被害人的鲜血,写下整整十年前的日期,这才是巡捕房邀请你来协助的原因吧。那一年,从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徐福丸失踪,船上的庚子赔款不翼而飞,一百万两白银的巨款,就是这桩大案吧?”
“对不起,恕我不能详说。”叶克难盯着秦北洋的双眼,“刚才我躲在暗处,偷听你俩的对话有一会儿了。你们分析得有道理。”
齐远山忍不住问:“案情可有进展?”
“尽管工部局董事会、各国驻沪总领事都限令尽快破案,但巡捕房依然束手无策。我向其陈述了八年前天津徳租界灭门案,还有今年北京监狱大屠杀的所有细节,甚至从档案柜里带来了当时的凶器——象牙柄嵌螺钿‘彗星袭月’的匕首。”
“就是这把匕首,杀死了我的……娘亲。”
秦北洋没有说养母,还是说“娘亲”二字,可见当年凶案对这孩子伤害之深重。
“嗯,这是刺客唯一留在现场的凶器,我想可能是打开谜底的钥匙。”
“叶探长,那你今晚来到这里勘查现场,有什么特别发现吗?”
“有!”叶克难沿着这条街往东走了几步,“从这里一直走下去,会是什么地方?”
“黄浦江边的码头。”
“当天凌晨屠杀劫狱之后,你说刺客们究竟往哪里跑了?那个叫小木的盗贼,现在被藏在什么地方?为何公共租界联合法租界与华界都查不到任何线索?据说巡捕房把苏州河以北的上万户人家都翻了个底朝天。”
秦北洋被叶克难的提醒开了窍:“如果……他们当天凌晨就上船走了呢?”
“也许还没走!”
“对,他们既然还在监视我,就不会放过海上达摩山和小镇墓兽的。”
齐远山又插了一嘴:“我猜,那些人还在上海,也许就在停泊码头的船上?每艘船都悬挂外国国旗,除非有直接证据,租界当局不能上船搜查,青帮也不敢惹外国人,这就成了刺客们可以利用的缝隙。”
“不错。”叶克难拍拍他的肩膀,“我觉得这案子,一时半会儿还破不了。”
“既然是来协助破案的,你跟青帮老大欧阳先生谈过吗?”
作为欧阳思聪的徒弟,齐远山更关心师父的心思。
“今天刚聊过。他说起幼麒麟镇墓兽的来历,在汉口倒卖文物的军阀名字,我会通过内务部的关系去调查。欧阳先生还说——谁拥有了那只小镇墓兽,谁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厄运。”
秦北洋打了个寒战。凶案现场的街头扫过一阵阴风,枯黄的梧桐落叶诡异地旋转。
突然,齐远山感觉有人在摸他的脚后跟:“不要留在这个鬼地方了,我感觉一群印度人的鬼魂飘过来了……”
叶克难就此别过,最后警告一声:“办案经验告诉我,除非你是警察,否则不要轻易回到凶案现场,说不定你会和凶手狭路相逢。”
“我还盼着这一天呢!”
深秋里,秦北洋捏紧拳头,为了复仇,他就怕刺客们不再出山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