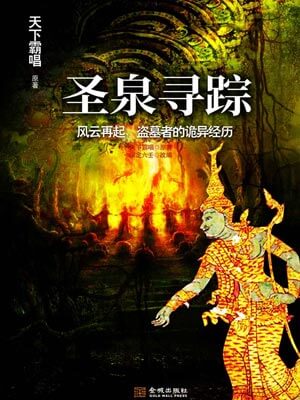已近子夜,回到海上达摩山,秦北洋累得筋疲力尽,换了身干净衣服,经过二楼走廊,听到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像太行山上的山涧。
二楼有个琴房。欧阳安娜正在弹琴,月光隔着银杏稀疏的影子,脸颊上两道清亮的泪痕。
“谁?”
钢琴声戛然而止,安娜抬起手指,看到了他的脸。秦北洋并未逃窜,攥着块手帕走进琴房,笨拙地塞入她的手心。
“你去哪儿了?等一等……”欧阳安娜靠近他嗅了嗅,“身上有酒气,头发还有点湿,你莫不是去了四马路?”
四马路就是今天的福州路,既是旧上海文化人钟爱的书店街和出版街,也是妓院云集的红灯区。秦北洋想起晚宴就在四马路上的老正兴,自是百口莫辩:“我掉进苏州河里洗了个澡,你信不信?”
“瞎七八搭!你可别骗我。今晚爸爸不在家,我睡不着。”欧阳安娜没说爸爸是四马路的常客,“我在弹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今天,是我娘的五周年忌日。”
他沉默好久才说:“我娘已经死了十七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
“对不起!你从不记得妈妈的样子?有她的照片吗?”
“她哪里拍过照片!我爸一辈子都没拍过一张照片,我也没拍过呢。”
“天哪,你是从古代来的吗?”
秦北洋却瞪着她说:“在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都还停留在古代。”
话音未落,隔壁响起一声清脆的玻璃碎裂声。静谧的子夜,这声音差点刺破安娜的小心脏。
九色!
她推开秦北洋,找到钥匙,打开私家博物馆的铜锁。她竟看见一条大狗——红鬃白毛的松狮犬,站在破碎的玻璃前,知道闯了祸,双目惊恐地后退,尾巴夹在双腿之间。
安娜刚要尖叫,却被秦北洋堵住嘴巴。
“九色!”秦北洋像教训牲口一样教训这头镇墓兽,“你又调皮了!”
说话之间,大门却被推开,一个人影闯进来,打开吊灯,白光刺得他俩睁不开眼睛。
“你们在干什么?”
齐远山看到秦北洋捂着欧阳安娜的嘴,还有一条红鬃白毛的“大狗”。他早就怀疑秦北洋和小镇墓兽有特殊关系。有时半夜在府邸巡逻,就会听到二楼有奇怪的声音。
转眼间,这条大狗已跑回玻璃柜子,变成幼麒麟镇墓兽,重新露出青铜外壳与鹿角。
“远山,你能不能发誓?”秦北洋抓住他的胳膊,“替我们保守这个秘密,永不泄露!”
欧阳安娜像被老师抓到早恋的女中学生,又补一句:“尤其不能让我爸知道!”
“安娜,你也要发誓!”
面对秦北洋的眼睛,欧阳安娜与齐远山都发誓保密。秦北洋这才蹲下来对小镇墓兽说:“九色,请你出来吧。”
于是,三人目睹这尊幼麒麟镇墓兽,不但睁开眼睛,眨动眼皮,还能转动脖子,抬起四条腿和爪子,甚至甩两下尾巴。头顶的鹿角慢慢放下,收缩折叠,藏入赤色鬃毛深处。身上的铁甲鳞片,变成豹纹似的斑点。青铜也柔软下来,像春秋战国的皮甲,竟长出一层薄薄的皮肤,覆盖白色偏灰的绒毛,唯有鬃毛与尾巴仍是火焰般的颜色。
九色摇身一变成了奇形怪状的狗。仿佛成为满屋子古物的主人,检阅唐三彩的仕女与武士、汉朝王陵的木俑军阵,还有辽代木雕佛像——每一个古物也都在看它,甚至嫉妒它的自由。它像四个月的老虎、五个月的狮子、六个月的公牛,满地打滚儿咬尾巴,蹿来蹿去。安娜感觉像做梦,用力按了按九色后背,摸到这一层雪白皮毛下,坚硬的青铜鱼鳞甲片。
“唐朝匠人制造这尊镇墓兽时,就在身体里安装好了。”秦北洋抱着九色的脖子,“它的鳞甲片可自动打开,就像人体皮肤的毛孔长出毛发来。而在青铜甲片关闭时,这身白毛就自动缩回到甲片下。”
“鹿角呢?”
秦北洋抓住安娜的手,指引她深入九色的火红鬃毛,触摸到几节坚硬的条状物。
“就像折叠的西洋伞!你说它不吃饭不喝水,哪来的力气动呢?不符合科学规律啊!”
“它也不拉屎撒尿!地宫里出来的东西,一定会带有我们不知道的力量。”
“你也是!秦北洋。你身上有太多的秘密,像一座埋在地下的坟墓。有时候,你的眼神像死人一般可怕。”
秦北洋故意翻了翻白眼,惹得安娜的拳头在他胸口乱捶:“别吓唬我!”
齐远山看在眼里,低头要往外走,却被秦北洋叫回来:“远山,我造过许多石像与木雕,半夜月圆时分,它们都会悄悄动起来。按我爸的说法,这是能工巧匠的灵气。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传递力量。不管石头、木头还是陶瓷,凡是具有动物或人体的形状,都会产生灵魂,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发生反应,甚至有自己的意识与情感。”
欧阳安娜汗毛凛凛地看着私家博物馆的各个玻璃柜子,仿佛那些唐三彩人物、西汉的木俑军阵、辽代的木雕佛像,全都千变万化起来:“你是说半夜里,他们会开一场盛大的Party?”
“说不定夜夜笙歌!我相信九色有它的灵魂与七情六欲。”
九色后腿直立扒在窗边,眺望天上的月亮,也许在回忆唐朝往事?
“只有在地宫里陪伴墓主人,镇墓兽才是真正自由的。”
秦北洋低声说。月光隐入云层,结束这漫长的折腾。
这一昼夜太神奇了,白日虹口柔道馆对决,黑夜在外白渡桥推手坠入苏州河,再回到虹口巡捕房凶案现场巧遇名侦探叶克难,子夜在海上达摩山九色露馅……
次日起,安娜开始教秦北洋画画。这些天,欧阳思聪都在外地打理生意,反倒让家中的少男少女们,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毕竟是工匠出身,雕刻花鸟虫鱼才子佳人都是基本功,秦北洋很快掌握了素描基础,竟能用炭笔画出三英战吕布。他又跟安娜学习油画,这才知道了保罗·高更、文森特·凡·高、保罗·塞尚……两人躲在三楼的画室,经常画得满脸油彩。
安娜发现他的手掌心全是老茧,硬得像一层天然的盔甲,摸上去都有些心疼。秦北洋把手缩回去说:“没有一手的老茧,哪能做个合格的工匠?”
“你就想一辈子做个工匠?”
“嗯……这是我唯一的志向,做个默默无闻的匠人,跟文物待在一起,修修补补家具和钟表。”他看着自己的油画说,“海上达摩山里的宝贝,包括幼麒麟镇墓兽,还有辽代木雕佛像……它们难道不是顶尖的艺术品?可你叫得出任何一个作者的名字吗?”
欧阳安娜瞪大双眼,无可反驳。历史上真正的天才大师,都没留下过名字,或者说,都是默默无闻的匠人,就如眼前的少年。
作为教他画画的交换条件,安娜希望秦北洋教她开枪射击,说要在乱世中学会自卫。
秦北洋却拒绝了:“我讨厌杀人,不想看到你拿枪。如果,一定要有个人来保护你,那么我可以。”
“你能保护我一辈子吗?”
此言一出,秦北洋分外尴尬脸红,他已不是小孩子,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摇摇头就逃跑了。
隔一日,欧阳安娜跟齐远山去江湾沼泽地,让他教自己开枪打靶。
齐远山并不推辞,他在荒野里做好标靶,手把手教安娜如何用枪,如何保养甚至拆卸复原。他的枪法极好,不但射中靶心,还打中好几只野物,但安娜让他不要杀生。齐远山与她几乎脸贴脸矫正姿势,但并未趁机轻薄小主。他和秦北洋都是十七岁,但齐远山的眉眼与说话都像成年人,明白人情世故,懂得乱世生存之道,也更野心勃勃。
“齐远山,你怎么看待我爹?”
“欧阳先生是我的师父,顶天立地的英雄,我辈做弟子的唯有努力侍奉师父以及小姐。”
安娜蹙起蛾眉:“最讨厌这些客套话!我不理你了。”
“好吧,每次我看到你爹,都会打心底里害怕。”齐远山拗不过,只能说出真心话,“人说伴君如伴虎,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也会得罪他,无声无息地从世界上消失。”
“我爹就是个混世魔王。”安娜举枪射出一发,不知击中什么东西,后坐力让手腕发痛,“十年前,他还是个海盗!”
“1907年9月2日,失踪在东海上的日本轮船——庚子赔款的百万白银,真的跟你们家有关?”
“对不起,这些秘密,不能告诉你!”欧阳安娜将枪口对准他的眉心,“齐远山,你就像一棵粗壮的小树,早晚会长成参天大树。”
秋风吹过江湾野地的芦花,芦花漫天飞舞如大雪,几乎蒙住少女琉璃色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