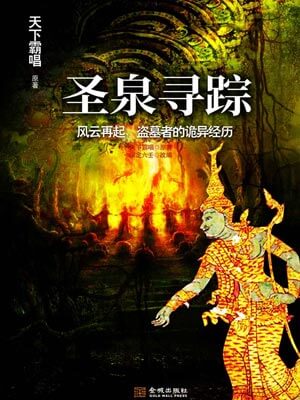被巨蛾迎面一盯,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树端待得太久了,已经暴露了目标。几乎就在吐吸的片刻间,那巨物振翅一扇,无数灰白色的鳞粉如下雨一般劈头盖脸地朝我这边卷了过来。因为不知此物是否带毒,我不敢小觑,看准了后路,翻身一滚,直接扑入了密林茂枝之中。那东西虽然巨大,毕竟是天上飞的,一时间无法穿透枝叶,我抓住这个机会一溜烟地蹿下树去。开玩笑,这鬼地方到处都是银茧,谁知道一会儿有多少幺蛾子要扑出来。我手上没有武器,四下更没有支援,不至于傻到冲过去跟它死磕,常言道,双拳难敌四手,人家可不光有手,还有翅膀。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最近落过雨,我一落地就踩了满脚的烂泥巴,差点摔倒。不过片刻也不敢耽误,抬头看了一眼那东西的动向,果真是叫密不透风的树冠绊住了手脚,一时无法靠近地面。我拔腿就跑,专挑道窄林密的岔路走。那东西一直在我头顶上跟着,没有一丝松懈。我心里明白,这样逃下去不是办法,必须要想一个脱身之策,而关键是与大部队会合。只是我初到雷公岭,此刻连方向都无法辨别,想从此地突围简直比狗嘴里抢包子还难。急智之下,我想起阿铁叔说过我们此行的目标是翻山索道,人马和货物都要从索道走,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对岸。当时他也说过,我们的位置离索道不过数百米,我被诡丝拉上山崖不过十来分钟,只要能摸到主干道,顺着山势一路往下走,必然能找到马帮的行踪。
打定主意之后,我不再犹豫,鼓起一口气,准备冲出树林寻找生机。空中不断有银色的粉末往下落,这说明巨蛾还在上头盯着。我实在不明白,如此巨大的生物,是如何在此地生存下来的。江城离这里不过半日路程,又常有旅人从山上借道,刚看它们的幼虫在山道上以诡丝捕食银茧做笼,整个过程熟练老道,是它们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捕食本能,绝非一日之功。如此巨大的体积,它们平时到底是以何为食,为什么附近的居民,假道的商旅从来未受到过攻击?
我始终觉得,马帮被袭击一事不合情理,只是一时间,思绪太过混乱,又忙着逃命,实在想不出个所以然。这时,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从我头顶上传来,抬眼一看,好家伙,原来这里的树端上同样缠着一只银茧,此刻正摇摇欲坠,只怕又有巨蛾要破蛹而出。我一看此地不宜久留,想也没想转身准备离去,却看见银茧底部忽然燃起一阵火光,刚才那阵异响就是银丝燃烧时发出的。我见其中蹊跷,心生疑惑,也不急着逃,快速巡视了一下四周,从地上抄起一根朽坏的树枝朝着火的银茧上捅。一戳之下,居然听见里头有人喊疼。我心喜,看来这位兄弟还未化作蛹食。当下又猛地挑了几下,想赶紧把那东西从树上弄下来。不想火焰越烧越旺,我在树下都被烤得两眼发疼,再不抓紧,估计里头那人不被蛾子的幼虫吃掉,也要葬身火海。里头的人似乎也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冒着火光的银茧像一只大红灯笼,不断地晃动。很快在大火和晃动下,银色的虫茧底部裂开了一道焦黑的活路,还没来得及看清掉下来的人是谁,就觉得头顶上一重,我整个人后背朝下被压倒在地。那一下磕得我,脊椎都快撞断了,疼得哎哟哟地直叫唤。
“老胡?”我身上压着的人,满脸黑灰,身上的衣服差不多都烤化了。唯有一副眼镜,在黑夜中贼亮贼亮的。
我一把将他推到边上,问道:“你他妈怎么也在这里,这火怎么回事儿?”
秦四眼死里逃生,他看了一眼在树端燃烧的破茧,笑道:“我看你被抓上去之后,也学着你的样子,拉了一下银丝。这不,就被困住了。”他指了一下脖子,那里全是血,又红又肿,“要不是随身带着打火机,恐怕咱们现在也说不上话了。”
我见他身上除了被咬伤的痕迹之外,暴露在外面的皮肤上有几处已经冒了水疱,尤其是手臂上,皮肉红现,如果不及时消毒包扎,很可能会留下隐患。此时破茧因为火力猛烈,终于挂不住,整个摔了下来。我忙将四眼拉到一边。
“灭火。”我脱下外套,冲了上去。这地方到处都是易燃物,随便引一个火星就能引起森林大火,必须趁现在立刻扑灭。四眼也明白其中利害,立刻跑上来,先是将地上的枯枝烂叶抛去,接着用脚猛力地踩踏火茧。我俩忙了半天,好歹是把燃烧中的银茧灭了个干净。
四眼喘着气,看了看伤口,对我说:“这地方太危险了。我看八成是虫窝,快走吧。不知道马帮那边怎么样了。”
“出了林子,找大路,这种地方如果真有索道,必定不可能藏在密林里头。应该是比较空旷的地方,然后还要有结实的基石打底。”
四眼点点头:“我们现在的位置,大致在雷公岭三分之二的地方。阿铁叔他们说索道在山腰上,我们如果能回到来时的盘山道,速度就快了。”
我说你先别忙着走,伤口稍微处理一下。我背包里有水、酒精和纱布,都是从江城林家的铺子里弄来的。在野外走惯了,身上不准备一点儿应急的东西,浑身不舒服。胖子老说我这是瞎操心,这下事实胜于雄辩了,可惜,他人又不在。待会儿下了山见了人,可得让四眼现身说法,给他一记警钟。我让四眼把身上那些破破烂烂的布头都扒了,然后用清水给他冲了伤口,酒精也不敢直接擦上去,只在一些边缘处,把碰上泥土的部分大致清理了一下。最后将我的外衣脱给了他。迅速地做好了这些工作之后,又用破损的衣料和酒精做了一个简易的火把,我俩这才上路,去寻找大部队的人马。
一路上,四眼跟我谈论起雷公岭的巨蛾,都觉得不可思议。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突然冒出来的?”
“不太可能。”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它们靠什么为生?你也看见了今天的场面,绝对是肉食性昆虫。”
四眼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我嘘了一声,抬头去找那只一直跟在我身后的白蛾子。转了一圈,天空中没有找到一点儿踪迹。奇怪了,刚才还虎视眈眈一路尾随着我,怎么四眼来了之后,它倒销声匿迹了。我看了看四眼,此刻上半身光罩着我的大外套,手臂上包着纱布,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不像有什么驱虫秘方的样子。
他见我看天,也跟着停了下来,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将蛾子失踪的事跟他说了一下。四眼沉思了一下,说:“你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它怕的不是人,是火?”
听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非常有可能!刚才我在扑火的时候,的确没有再看见粉末飘下来,这说明它当时已经不在现场了。这之后,我们一直在救火,起码到刚才为止,也没有见到它的影子。我看,这种巨型蛾八成是畏火,早就逃远了。”这可真是天下一大奇闻,从来只听说过飞蛾扑火,这雷公岭上的巨蛾偏偏背道而驰,刚发现火星就逃了,静心一想,不可谓不聪明。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盘山道的痕迹,四眼指着前方的火光大叫:“那里有人。”
我一看的确是篝火驻在山崖间,知道这是阿铁叔他们在下边,立刻带着四眼朝山道跑了过去。没一会儿,马帮的队伍就出现在我视线范围之内。那边的人,也明显感觉到山林里的火光。查木第一个看见我们,他激动地跳了起来,大力地朝我们挥手。
队伍里的人,见我们从山上头走下来,一个个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杨二皮原本坐在火堆边上,一听见有动静,立刻拔出了手枪。我怕他冲动之下,乱放黑枪,只好大喊道:“是我,胡八一。”这一声不只喊给他听,更是喊给其他人听。如果老东西想乘乱放枪,必然有所顾忌。果然,香菱和阿铁叔同时站了起来,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查木这小子快步迎了上来,一张黑脸,不知道是哭还是笑,一把抱住我说道:“你们可真吓死人了,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读书人怎么了?怎么都是伤?哎,胡爷,你的衣服怎么不见了。对了,你们到底去哪里了,怎么一眨眼……”
我被他劈头盖脸地一问,一时间也不知道先答哪个好,只说我们两人不碍事,先见了阿铁叔再说。查木忙点头说“好”,拉着我和四眼快步向山间空地上的篝火营走去。走进一瞧才发现,队伍里的人又少了几个,杨二皮的伙计只剩下三个人。一个个都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仿佛见了鬼一般。我也没多问,径直走到阿铁叔面前,对他说:“失踪的事,我弄清楚了。是山间的巨蛾幼虫在捕食,它们用韧丝做饵沾在人肩头,趁人不备的时候,就发力提上山去,当做卵化用的食物。我们刚才差点死在虫茧里头。山上的林子里已经有不少成虫孵出来,这里太危险,还是早点撤出去为好。”
阿铁叔的脸色在火光下显得尤为凝重,他听我说完山顶上发生的事之后,静静地坐了下来,叹气道:“这么说,我的人都是叫山上的幺蛾子给裹去了。妈的,老子跑道这么多年,雷公岭这块地方,恨不得每一块儿石头都摸着走过。怎么偏今天,遇上这样晦气的事?”他说完,瞪了杨二皮一眼。那杨二皮先前一直站在我们边上,有意无意地将我讲的事情都听了去。此刻他面色不善,几次想开口,最后都憋了回去。后来才知道,他那一串拴在一块儿的伙计,果真是叫山上的诡丝吊了上去。好在带头的人聪明,及时将腰间的绳子割断了,死里逃生。要不然,杨二皮这趟就真成光杆司令了。
香菱见大伙都不说话,将手中的柴火一丢,带头发言:“咱们都走到这里了,索道近在眼前,哪有不走的道理?既然山上的怪物怕火,大家只管把火把都竖起来。我一个女人都不怕,你们一个个傻坐着孬不孬?”
“我呸!”有一个养马人忍不住暴跳起来,“老子才不是怕它,老子要上山,给兄弟们报仇!”他说完,取出腰间的弓弩,作势要走。立刻有几个人也跟着他起身,嚷嚷着要放火烧林,把那些东西逼出来,给死去的马帮众人垫背。眼看局势要乱,就听一声巨吼:“这铁马帮,到底我做主,还是你们做主!”
阿铁叔一跺脚,所有人都震住了。此刻他脸色铁青,眼睛瞪得有牛大。他抄出腰间的猎枪,环视众人:“咱们是马帮,不是土匪。当初入伙的时候,签好了生死状。这个仇要报,可不是现在报……咱们跑马的,信誉比命重要,答应了人家,明天太阳升起来之前要到抚仙湖,那说什么也不能拖,必须在太阳上山前送到。豹子你要去给兄弟们报仇,我第一个点头,可这事现在办不得。所有人听我的,立刻收整东西,查点货物,牵上骡马。咱们过索道下山去,等回来的时候,老子把这片山头铲平了给你们看。”
阿铁叔说话,根本不容其他人反驳。四眼咋舌,朝我比画了一个大拇指。我又想起在黄皮子坡上,跟胖子大开杀戒的那一年。所以阿铁叔此刻心情,我非常理解。杨二皮似乎没有想到阿铁叔还肯走下去,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走到篝火前,朝大伙拱手:“各位朋友,今天这一趟,是我杨槽对不起诸位,死去的兄弟,算我的。待来日,我与诸位一同上山,为他们报仇。”
阿铁叔对他摆手:“生意是我们自己接的,怎么能因为出事了,就迁怒别人。铁马帮没有这样的人。你叫自己的人小心,货物查点好,我们现在要去下索道。”
我当时只觉得这次杨二皮仗义过头,可能藏有猫腻,直到下山之后才发现,这家伙分明是话中有话,深意暗藏。
我一路上都在听大伙谈论雷公岭索道,眼下就要见到它的庐山真面目,不禁有些激动。先前带头哗变的豹子听了阿铁叔的话,走到空地边缘处,他高举火把,将山壁上的树枝一把扯落下来。我早就奇怪,为什么寸草不生的山道上,会有一处布满枝叶的角落。没想到原来是马帮做的掩体。
阿铁叔解释说,这个掩体的作用其实并不是为了隐藏索道的位置,他指着嵌在山崖上的单线钢丝说:“你看这个锁头,要是不好好保养,用不了几趟就要出危险。我们的人会定期上山检查更换索道配件,这些树枝是用来防风挡雨的。你别看这玩意儿简单,飞渡直下,过了山下的婆婆溪,就是苗区了,比平时翻山节约了十几倍的时间。”
我遥望了一下山脚下,果然在南麓有一处河溪,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查木兴奋地为我们介绍起这条他小时候光屁股摸虾的母亲河。据他说这是月苗寨附近最大的一条溪河,寨里人吃喝拉撒都离不开这条婆婆溪。而溪面上,此刻如星河一般璀璨的是他们寨子里特有的捕虾方式——放河灯。利用的是河虾向光的原理,捕虾人在溪面各处插上削好的木桩,以木桩为中心,围一圈尼龙网,最后将灯泡挂上小电机,拴在木桩中央,一般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收网,捕上满满一网的虾子。
“以前都是用煤油灯,最近才改用电机,一个电机能连十几个灯泡。方便着呢!”查木说着扯了扯钢丝,准备第一个下索道。阿铁叔一下子将他拉住:“你个子小,不能当先锋。香菱,把筐给我,我先下。”
阿铁叔负重而行,是为了确定钢丝能够承受所有人的重量,查木毕竟是个少年人,也就一百来斤的模样,他过得了索道,不代表其他人也能顺利通过,更何况队伍里还有马匹和货物。四眼说没想到阿铁看上去粗陋,心思却十分细腻,连这些容易马虎的细节都注意到了。我点头,小心使得万年船,就算平日里有人会上山检修,也难保它关键时刻不出意外。
阿铁叔将一支铁打的双头挂钩,用棉布抱住手握的一头,然后又在连接索道的那头抹上了油脂。我问香菱既然知道单向索道危险,为什么不再安一条,并成双股的,好歹结实一些。她想了想回答说:“你看锅头腰间挂的那一节钢丝,待会儿滑过去,连在对岸不就成了双向的?”我不解地问:“既然这样,那一开始就做成双向索道不就好了,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每次冒险?”香菱咬了一下嘴唇并没有回答我。四眼拉了我一把说:“马帮说穿了是运输业的一个分支,他们挣钱,走的都是常人走不了的路。如果此处的索道修成双向的,就会减少路途上的风险,必然有其他人愿意冒险一试。”
我点点头,他这个分析很有道理,要是天底下的人都能一夜飞渡雷公岭,那等于断了马帮一条财路。单行索道不但危险,而且有去无回,一般的商旅是断不敢轻易尝试的。马帮每次渡索道,都要先派一人在山这头将另一道钢丝接好,等那人带着钢线到了对岸,只要将锁头连接好,就能形成一个简易的双向索道。最后一个人走的时候,再将第二道钢丝撤去。这样一来一往,断了别人的路,发了自己的财,不可谓不是用心良苦。查木在一边听了我们的分析,恍然大悟:“我说怎么每次都要拆来拆去,锅头真是聪明。”
我心知这些跑马人苦钱不易得,也未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有些担心,单行索道,靠的是向下的重力和引力,一旦他们想从对岸折回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要是遇上什么突发状况,那可怎么办。正想着,阿铁叔已经整装待发,他朝豹子等人比画了一个拇指。然后高呼一声,拉住挂钩,双脚在崖边一蹬,如同一只脱笼的猛虎,一下子飞了出去。看着阿铁叔健硕的身影,大家都忍不住跟着欢呼起来。香菱用手搭在额头上,张望了一下,回头说:“再过去一个人,帮锅头拉绳子。剩下的人,把马匹和货物捆结实了,等双行道准备好了,咱们就走货。”我问她马匹和货物要如何从这万丈陡崖上运过去,陆地上的牲畜,生来就惧高。马匹也不是什么温驯的动物,要是它们半道上乱动出了闪失,那不是连救的机会都没有?
豹子白了我一眼,粗声道:“俺们的马不比你们那些汉人的娇气,别说过索道,下火海都不怕。你待会儿看着好了,我这匹黑云上去之后要是敢乱吼一声,我这趟的工钱全分给你小子。”
听他的口气虽然像在故意找茬儿,但我知道他其实在恼杨二皮惹来的麻烦。他火急火燎地赶这趟货,凭空叫马帮折损了兄弟,豹子碍于锅头的威严不敢当面叫板,只好没事找人来吵两句以求发泄。所以我心里虽然有火,但也不愿跟他当场叫板。查木看不惯,上前阻劝,反倒被豹子劈头盖脸地教训了一顿。
“才结识多久的人,你倒替他说话。这些汉人又奸又诈,特别是那个老头尽给大伙添麻烦。查木你到底是站在哪边的,是不是收了人家好处?”
查木被气得两眼发直,我见不惯这种不讲理的人,沉下脸来,挡在他面前。
“你,你要干吗?”
我抬手就是一记耳光,那豹子早有防备,速度却没有我快,凭空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刮子,正要发作,又被我一声巨吼:“你多大的人了,跟一个孩子闹别扭。你怎么好意思现在起内讧,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对得起对面的马锅头嘛!”
这招叫做先声夺人,诀窍就是必须在敌人发作之前,从气势上压倒对方。把对方吓得没了火气,你自然而然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这是胖子总结出来的几大神技之一。我活学活用,给豹子来了一个下马威。其他人本来正在整理行李,准备下索道,一听见我们这边闹开了锅,纷纷朝这边看了过来。豹子涨红了脸,一时间不知道要如何辩解。香菱忙上前解围,她两手一伸,用力地捶在我二人肩头:“好了好了,都什么时候了,两个大男人,也不害臊。豹子,待会儿你先过去,帮锅头在对岸接货。胡大哥,你以前下过这种索道没有,我找个人教你?”
我不好意思拿人家小姑娘为难,就顺着她起的话头把谈话内容接了过来。我告诉她自己对双向索道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派两个人去教杨二皮那伙人才是真的。
说起杨二皮,好像自从我回来之后,他就没怎么开过腔。难道老东西转性了?被山上的巨蛾一吓,吓老实了?不能够吧,再怎么说也是走南闯北,几十年大风大浪走过出来的槽帮巨头,死几个人就认了?我忍不住朝杨二皮几人看了过去,发现他们正团在一处低声密语。杨二皮脸色泛青,似乎正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一边说话,手一边在微微颤抖。我本想靠上去看一看,却被四眼叫住。原来他从未有过横渡索道的体验,此刻看着脚下黑黢黢的断崖,心中惶恐,要我教他。
我说这事其实跟学游泳一个道理,没下过水的都怕把头埋进水里,呛过一次自然就不怕了。索道也一样,你试一次就知道了,这事比吃饭难不了多少。四眼“哦”了一声,又问:“那万一摔下去怎么办?”
我思考一下,说:“那可就没办法了。要不你留张字条下来,有什么要说的,我回头替你转达。”
四眼当场朝我屁股踹了一脚,我哈哈大笑,跟他说这都是玩笑话,帮他放松心情而已。这个时候,豹子和阿铁叔已经相继到达对岸,他们在对面扬起了绿色的三角旗。香菱在这头也挂起了同样的旗帜。她回头对剩下的两个养马人说:“索道已经上结实了。你们把马拴紧,准备过去。”只见其中一个黑胖墩点了点头,将一匹五花大绑的货马赶到了悬崖边上。那高马似乎早已习惯了跟随马帮翻山越岭,搭索道走险滩,此刻面对陡峭的崖谷没有半点儿惊慌,一直安静地站在那里,随他们几个养马人摆弄。没多大会儿工夫,裹在马匹身上的皮带扣就被挂上了索道下面的悬吊处。我问香菱是不是要找一个人和马一起过去,她怪我没见过世面,笑道:“怕什么,都是老马,习惯了。再说太重了索道也受不了,更容易出危险。”
说着,就见两个养马人相互做了个手势,齐声喊了一声号子,将货马推了出去。
虽说经验老道,可毕竟摆脱不了生物的本能,那匹白马被他们一把推出山崖,整个身子一沉,四蹄立刻在空中飞快地奔腾起来,不断地发出嘶鸣声,看样子被吓得不轻。山下河溪对岸,阿铁叔和豹子两个人,戴着木工用的粗线手套呼哧呼哧地拽着绳索往自己那边拉。我见马帮这边并不需要帮助,就转身去看杨二皮那边的情况。
大概是因为刚刚的意外,眼下马帮里居然没有一个肯主动上来帮他准备过河事宜。杨二皮青着一张老脸,抛不下面子出来找人打探下一步动向。我瞧着两边这个架势,只好上去做和事老。杨二皮见我朝他们走了过去,立刻迎了上来,不过并不主动开口说话,看来还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主。都闹到这步田地了,愣是不愿意放下那副盛气凌人的前辈架子。
我也懒得跟他计较这些虚的,只当帮阿铁叔做好事,赶紧把杨二皮连人带货送到山下去。等我们进了月苗寨,就跟这老贼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到时候,他就是天王老子,大爷我都不会答理半句。
“杨老板,准备过索道了,你们这边的伙计,都准备好了吗?”
杨二皮见我对他开腔,立刻把台阶顺了下去,摆出一脸假和善:“托胡掌柜的福,这些小的们早就整装待发,准备好下山了。不知道,铁锅头那里……”
“马已经过去了,马上就要运货了。杨老板,先前在江城,我怕人多嘴杂,不方便。你看现下发生了这么多事,也没有外人。您是不是方便透露一点儿消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看你这趟走的货,不一般啊!”
杨二皮两眼忽然一瞪,旋即又冷静下来,继续打哈哈:“哪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是受人所托,去送点货。至于在江城的时候,哈哈哈,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我一时眼花,并未认出胡掌柜的来。”
我见他实在不愿意坦诚,也就不再勉强,让他将手下两人招呼过来,把过索道要用的挂钩和皮带交到了他们手中,又示范了一下如何使用。杨二皮连声道谢,带着人直奔山崖口而去。四眼问我是不是探到了什么消息,我说这老东西狡猾得很,得了便宜还卖乖。既然他不想说,咱们也别多问了,过了索道,大伙分道扬镳。他就算运的是满箱的老粽子,也挨不着大爷半根汗毛。
四眼对涉及人身安全的事习惯亲力亲为,他在一旁将我俩要用的装备上下检查了许多遍,就差用牙咬了。最后很笃定地对我说绝对安全。我俩走到崖口,发现大部分的人员和马匹已经运到了对岸。杨二皮再三强调他要殿后,看着货物全部安全抵达对岸才肯跟上来。我和四眼只好身先士卒,先去对岸接应。不过,我对杨二皮这个古怪的提议充满了疑惑,总觉得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我和四眼一到对岸就被阿铁叔稳稳地接住,他笑道:“好小子,第一次过山道,不慌不忙的。也没听你叫一声,是条汉子。你瞧那几个脓包,已经趴在地上不敢动了,哈哈哈。”
我其实小腿也在打战,一路上没敢朝底下看一眼。此刻见杨二皮那两伙计脸色惨白正抱着大树干呕,不禁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四眼就更不用说了,这小子怕摔了眼镜,根本就是瞎着眼被拉到对岸来的,人说眼不见为净,他落地之后才从衣兜里掏出眼镜戴上,见了旁人的窘状,还问我发生了什么。
阿铁叔将插在一边的绿旗拔下,换上了一枚黄旗。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货物差不多都齐了,让那边收尾的人准备收索道。”
此时,对岸响起了哨声,最后一箱黑木箱顺着双行索道一路飞驰而下,原本在岸边接应的伙计不知因为什么,并没有上前接住货箱。我大呼不好,只见货箱带着巨大的惯性一下子冲上了河岸,发出了一声巨响。停在边上的马匹受了惊吓,顿时变得狂躁不安,到处乱撞。马匹受惊不是小事,我在农村的时候曾经见过一匹发狂的成年马,掀翻一座农舍,破坏力十分惊人。阿铁叔深知其中厉害,他高喊:“一队人去接应对面的货物,一队人跟我去追马!”随后他高举马鞭,“啪”地一声在卵石滩上抽出骇人的声响。
我对驯马并不在行,立刻招呼四眼,让他躲到一边去,千万别挡在马匹前头。然后转身朝河岸跑去,想帮养马人照看刚才摔落下来的货物。我举着火把,蹚过溪流来到浅滩附近,因为货箱的撞击,原本遍布在河道上的虾灯已经被撞坏了不少,我只能依靠火把的光亮来寻找水中的货箱。走近一瞧,发现那一口木箱已经碎裂开来,要不是因为外头捆着麻绳恐怕早就散了。我蹲下身来,凑近货箱,想试着将它拖出水面,无奈这东西死沉死沉的,又进了水,一时间竟动不得半分。我回头看了一眼岸上,经验丰富的养马人正举着探照灯和鞭子,两两一组拉起绊马索开始对发狂的马匹进行围阻。四眼早早地爬上了一棵大树。
我见他们都腾不出手来帮忙,只好自己想办法收拾眼前的烂摊子。我将手伸进水里摸索起来,不知道是因为夜晚,还是河水本身就凉,手一碰到水里的箱子,就被狠狠地冻了一把,一股钻心的寒气从货箱破裂的缝隙透了上来。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就将脸贴近水面,想看看箱子里头装的是什么。我将火把移到近水的地方,自己俯下身子去看,可惜缝太小,又太黑,根本看不清楚,只隐约觉得里面那东西好像动了一下。我忙将手抽回,揉了揉眼睛。我对自己说,可能是河水反光产生的幻觉,因为我实在不相信有什么活物能在这样的箱子里存活。我不死心,使劲抬起箱子的一角,用脚在河床地下拨弄过来一堆沙石垫在货箱底下。这样一来,箱子破碎的那一面就被暂时抬离了水面,方便我确定刚才是否是错觉。这次我直接将捆在边角的绳子拉开了一截,箱面上的缺口立马散开了大半,一股绿色的烟雾腾空而起。我被吓了一跳,心说杨二皮怎么开始倒腾起化学武器了。也不敢再上前,一手捂着口鼻,一手拽起绳子,想将箱子捆回去。这时就听见我身后一阵狂吼,我急忙回身一闪,只见杨二皮满脸死灰,拼命一样举着枪朝我砸来。我不知他这是吃错了哪家药,手下不敢有丝毫怠慢,右手一挥,将火把挡在了面前。杨二皮竟好似浑然不知疼痛一般,一把扯了上来,也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大的力气,扣住我的手如同一把铁钳,“刷”地一下将我甩了出去。我整个人朝后一仰,后背重重地磕在箱角上,原本就摔得四分五裂的箱子根本承受不住我的重量,眨眼的工夫,连人带货物都跌进了冰冷的河水里头。杨二皮大吼一声:“不!”
然后,他立刻扑了上来。我当时呛得满鼻子、满眼睛的水,心里郁闷极了,老子好心帮你抢救落水的货物,你反倒偷袭我,早知道这样就把你这堆破箱子一把火烧了,省得事多。我一口凉水呛住了嗓子,差点当场溺毙。本以为杨二皮要落井下石当场办了我,不料,他竟好似没看见我一样,只一个劲地去捞那些碎木头。我从水里爬出来,浑身湿了个透,火把早就熄灭了,岸上的人已经平息了马匹的骚乱,纷纷往我们这边跑来。我咳了很久才将嗓子眼儿的河水吐了出来,也不知道那箱东西是不是有毒。我见杨二皮蹲在水中央,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全无方才的杀气,就走上前按住了他的肩膀。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怒道:“老年痴呆又犯病了啊?你到底想干吗?”
杨二皮缓缓地回过头来,脸上的皮肤不知为何像癞蛤蟆一样鼓了起来。他双手垂在水中,握着一样东西。我凑近一看,差点叫出声来:那是一只腐烂的断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