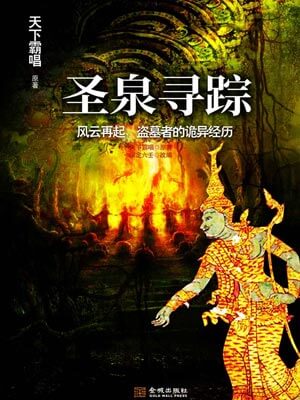我心想野人部落里边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宝贝,最值钱的也就是三眼黄金面具,而且都已经交公了。四眼奔至我面前,高举手中的卷宗,忍不住邀起功来:“我闲来无事,就去他们巫医生前住的帐篷里去翻看了一下,没想到,真叫我碰着了。你快看看,这里面有中文。”
我和胖子都以为自己听错了,急忙接过那本破旧不堪的羊皮卷宗翻阅起来,这是一本极厚的卷宗,分成好几个部分,已经被人用晒干的羊肠穿起钉了起来。卷宗的封面上赫然画着一枚形如弯月的摸金符。我来不及翻看,就已经知道全部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卷宗里面,一把抱住四眼:“大律师,你太伟大了!这件东西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四眼笑嘻嘻地将我牵到了篝火边,胖子和他害怕打扰我翻阅,都静静地坐在一边。我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来解读这本用克瑞莫语、中文,还有英文夹杂的羊皮卷,渐渐地将克瑞莫巫医的故事梳理了出来。
胖子一个劲儿地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啧啧称奇:“说出来你们不信,要不是有这本卷宗在手,我也不愿意相信世界上有如此巧合的事,这正是老天的缘分。”
四眼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掌柜的,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望着渐渐露出鱼肚白的天空,压低了嗓子说:“葬洞中的巫医与克瑞莫人并非同支,他们都是当地土著和一批清末淘金者的后代。”
我刚说了一句,胖子已经乐得合不拢嘴:“老胡,我还不了解你吗,又开始编胡话骗人了。就他们一个个长角穿洞的鬼样子,怎么可能是咱们中华龙脉的子孙。”
我摇头,拍了一下手中的卷宗,翻开其中一页:“这其中的变故都要从一座亚马孙丛林中的古墓谈起。”
清末年间,新思想的涌入给予了国人更加广阔的视野,有四个江湖跑把式的手艺人,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一个在南洋做买卖的生意人,搭伙坐上了轮渡,计划来美洲掘金。正所谓艺高人胆大,这伙人都觉得与其在国内穷一辈子,不如出海赌一把。当时那个南洋人对美洲的情况也是一知半解,连南美和北美都没分清,只知道听外国人说美国遍地是金子,生活十分幸福美好。结果一行人稀里糊涂地到了南美洲丛里,那四个手艺人再没有见过世面,也知道自己受了诓骗,南洋生意人为求自保,只好对他们说自己学过相地勘兴的风水术,已经在此地找到了一处外国皇帝的墓穴,只求大家同往发财。不过他没敢告诉其他人,自己的风水秘术是从说书先生嘴里听来的,只知道天下盗墓掘坟者,摸金最大。所以他就谎称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摸金校尉,能寻龙点穴,找天下丰葬之所在。
那四个手艺人只求能发财致富,也不管到底是挖金子还是挖古墓,就暂时放过了生意人。让他漫山遍野地找那处传说中的外国皇帝墓。也算他祖上积德烧了高香,几天之后居然真叫他找到了一处墓穴的所在。五个人自觉多福,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挖开的是一座魔鬼的坟墓。
故事说到这里,我就停了下来,四眼听得出神,催促我继续讲下去。我拍拍手,无奈道:“下面就没了。中文就这么多了,还都是白话文。剩下的尽是些乱七八糟的鬼画符。你要是能看懂,你看。”
胖子劈手夺过卷宗,前后翻阅起来,最后将它摔在地上:“这不是扯淡吗,讲了半截,后面就看不懂了。四眼你说,这是不是你闲来蛋疼,自己编出来的。”四眼大呼冤枉,我为他解围说:“我们上山也就那么一会儿工夫,他脑袋又没被门夹过。”我前思后想,将我对故事的后半截推断说了一下,这五个人可能是在墓中触动了什么机关诅咒,有一个人当场死在了墓中,落得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下场。其他人再也不敢走出丛林,害怕自己死后露出鬼角,被别人当成妖怪毁尸灭迹,最后只好留在异乡与当地土著通婚,又靠着坑蒙拐骗的伎俩当上了部落中的巫医,你们知道的,自古神仙啊罗汉啊,长得都跟寻常人不同。他们自封为天神的使者,死后回归天国,实则是为了掩藏自己死后变异的秘密。我捡起羊皮卷翻开一页破旧不堪的画卷:“你们看这个地图上的墓室,是不是觉得很眼熟?”
胖子眼尖,一眼认出这是我们刚刚爬过的巫医墓。“哎,这墓室底下怎么还有一层?”
我笑道:“不错,这个巫医墓只是一个顶盖,真正的墓室就藏在石窟底下,这是有人故意做了一个金鸡孵凤的风水局,想要混淆视听。”
胖子一听古墓比谁都积极:“我就知道,墓里边怎么可能没有陪葬品,一洞的尸茧吓唬谁呀!走,咱们快回去看看,说不定有一洞宝贝正等着咱们呢。”
四眼皱了一下眉头:“掌柜的,你不觉得这个地下墓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我怀疑,这就是那批清末掘金人最后挖出来的百鬼坑。”
我们三人沉寂了一会儿,决定一切等秃瓢醒来后再作打算。这一等就是三天,在王少的悉心照顾下,秃瓢总算是清醒过来。我把后来发生的事都向他讲述了一番。他也表示对那个百鬼坑十分感兴趣。我们将面具酋长提来问询,让亚洞与之交谈,再将谈话的内容用克丘亚语讲给秃瓢听,一个翻译连着一个翻译,听得我们旁边的人个个头晕眼花。秃瓢的伤还没痊愈,土著话的水平有限,不过倒是截获了一个重要的情报:酋长的面具是在三天前从一个黄皮肤男子手中用金杖换来的。
我急忙问金杖什么样,那男子长什么样子,为什么要用三眼面具换那个金杖?酋长被我吓了一跳,支支吾吾了半天,秃瓢说:“那金杖就是一根普通的棍子,是巫医平时用来大骂下人用的,酋长见他死了,又有人愿意用精美的面具来换,就答应了对方。”
我们都觉得这个黄皮肤的亚洲人很有可能就是一直在暗中与我们作对的竹竿子,而那根在克瑞莫人眼中毫无用处的金杖,可能对他另有大的用场,Shirley杨一路追寻杀人凶手而来,必然也在丛林之中。
四眼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坚决地说:“百鬼坑里还有很多的秘密,我想自己下去看一看,你们不必冒险。”
其他人异口同声地否决了我,胖子说:“老胡,你大大的狡猾,有钱分就想踹了兄弟们,门儿都没有。”剩下的三人纷纷应和,我只好答应一同前往,不过一切都是老规矩:听我的。
亚洞实在不愿意当我们的向导,于是秃瓢就给了他一些药物,让他回提他玛村去。胖子起了个坏心眼,揪住酋长说:“这小子是本地人,让他给我们带路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我想了一想,虽然语言不通,不过我们离魔鬼桥就只有数日的路程,竹竿子又快我们一步,带上他不是坏事,于是两人佯装恐吓了一番,将面具酋长提上马里克巢穴。
再度进入巫医群葬墓,我的心情与之前大不相同。先前,我们是抱着“到此一游”的心态想在外国墓中留个想念;眼下,我们得知了克瑞莫人死后异变的真正原因,心中不免产生了一种恐惧,同样都是摸金人、盗墓者,清末的那批掘金徒到底栽上了什么样的遭遇才会落得如此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凄凉下场,不但枉害了自己一条性命还祸及了子孙,白白断送了后人的福禄富贵。
我们一行五人,强压着克瑞莫人的酋长来到瓶颈洞中。秃瓢脑袋上有伤,我本来是不愿意让他涉险下洞的,无奈这个硬脾气的汉子跟我急红了眼,非要跟下来为他家王大少爷挡刀子。胖子说:“你这个狗腿子心态,死到临头了还惦记着主子。”秃瓢不置可否,强打起精神,忍着伤痛跟在了队伍后面。我心里明白,他这么做倒不是因为对王清正有多么的忠心,而是不愿意辜负了王家老爷子——天王老子王浦仁的一番信任。
面具酋长被我和胖子一前一后夹在队伍中间,他几次想借机脱壳,都被秃瓢用枪杆子挡了回来。我安慰他说:“下了洞之后,我们不用你做任何事情,你只要负责站在边上,别到处乱碰就是了。”秃瓢把我的话翻译了一遍,面具酋长听了之后面色发白,我估计他一定擅自加了几句狠段子来唬酋长,我不愿干涉他。只求这一趟能查个水落石出,带着所有人能平平安安地从百鬼坑中撤出去。
一落洞底,王少和四眼就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羊粪火把点了起来,插在葬窟的中央位置。巫医墓上窄下宽,空气流通不好,我担心氧气被消耗得过快,所以在上边的时候只准备了两支火把。胖子从包里翻出半截蜡烛对我说:“林子里的蜂巢老蜡,我让野人从蜂窝里刮来的,灯芯是用干草拧的,聊胜于无。老胡你凑合着用吧!”我接过胖子精心准备的蜡烛,从火把上借来火种这么一点,蜂窝蜡一下子冒出了白烟,小火苗颤颤巍巍地燃烧起来。
我将半截蜡烛立在巫医墓的东南角,对大家说道:“虽有形式主义之嫌,不过老祖宗的规矩立了,咱们照做就是。我们的礼数到了,待会儿要是出了乱子,动起手来自然才不理亏。”
四眼翻看起老巫医的羊皮卷,环视墓穴四壁,对我说道:“卷宗里只是大致记载了‘百鬼坑’位置,基本上能断定就在咱们脚下这块地方,不过入口在哪儿,如何得以进入,老巫医并没有记录下来。咱们好比是做贼的找不到大门,白想念。”
我说:“巫医墓和百鬼坑建在同一个地方,为的是一上一下做一个金鸡孵凤的风水局。既然是子母连心的顶盖式,那下面地宫的格局应该和上头这个群葬墓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秃瓢说:“你的意思是两个墓连在一起,找到群葬墓的活眼就能通到百鬼坑的入口?胡爷,容我说句泄气的话,老外的墓穴全无风水可言,这里又是蛮族墓葬,你能肯定其中有规律可循?”
我说:“在印度安人的概念里没有死亡一说,他们认为肉身死后,魂魄出窍是为了开始下一段生命。所以风水是肯定有的,总也没见他们把尸体胡乱丢在野地里任其腐烂不是。我们只能凭借百鬼坑的格局来推断巫医墓的样式,再从巫医墓打穿下去。就好比在下一盘盲棋。”我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给大伙打气,让他们心中有底;一方面也是在为自己梳理整件事情的脉络。在老外的地方上使用《十六字风水秘术》望穴相地,那是公鸡下蛋——自古没有的事。不光是我,往远了说,估计一人挂三符的张三链子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我挽起袖子,站在洞口,仰望星空:“南半球与北半球的地理状况各不相同,地势、水流、风向这些都做不得准。唯有靠天幕上的星辰来定位。”十六字风水秘术中开卷首推一个“天”字,我这个人实践一贯强于理论,对于“天”字卷中对星位、气象、黑黄二道的演推向来都是一知半解,只是嘴上的皮毛功夫。此刻真要用以探穴定位,心中还真是没底。不过大话已经放在了前头,众人手握工兵铲跃跃欲试都在等着我指定吉位,我也顾不上那么多,只好把生平所学的东西一股脑儿用上。马里克巢穴一峰独秀卓立云霄,走的是巽龙位,此龙本身就带着一股煞气,属木。清末的摸金人是为了克住煞龙,才将山间树木尽毁,又以熟石灰烧地使得这里百年难生寸草。想在这个地方取吉位,非要取天星阳玑也就是角﹑宿二星赤居其所在。这样一看,活眼的位置立马变得清晰可见。我丈量了一下葬窟的长宽,最后在被尸茧堆砌的西北角偏北的位置上定出了百鬼坑的入口。
面具酋长本来靠在火把边上,一直不敢出声。眼见我们要搬挪历代巫医的尸茧,立刻挥舞着大手上前阻拦,他拉着我的衣袖不断地苦苦哀求,秃瓢翻译说:“老红毛说巫医墓自古是克瑞莫人的圣地,巫医牺牲自我在此地镇守恶魔的巢穴。如果我们擅自移动尸体会遭到魔鬼的报复,巫医们的英灵也不会放过我们。”
王少一把拍开酋长的手,虎着脸说:“少他妈的贼喊捉贼,你们的巫医又长角又长洞,看着可不像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地下埋的那些玩意儿能比你们的巫医更像妖怪。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少杵在这儿耽误你少爷我干正事。”
此时胖子和四眼已经将大部分的尸茧移开,西北角凭空多出老大一块地方出来。王清正不甘落后,也提起一具裹尸,双手抱住尸茧底部开始往外移,秃瓢自然容不得他家少爷干这种粗活,要上前帮他。我本想上去给大伙搭个手,只闻王少忽然大叫一声,吓得我急忙举起手电朝他看了过去,只见秃瓢面带惧色站在离王少半米开外的地方,而王家大少爷正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我拿手电一照,只见他原本光滑细长的手臂上,布满了绿色的霉斑,如同一枚枚生着铜锈的钱币。而那一具被他摔在地上的尸茧外围也同样长着厚厚一层绿霉。
胖子道了一声:“你小子几天没洗澡,怎么都生霉了?”
四眼一脚踢翻地上的尸茧:“霉点子是从尸体上长出来的。这几具也有。”
王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急得又蹭又抓,恨不得将自己的胳膊整个儿卸下来。我按着他的双手对秃瓢说:“别傻站着,酒精,快拿酒精来。”
秃瓢恍然大悟,急忙翻开背包将小酒精炉取了出来,也许是太过紧张的缘故,他连拧了几下也没打开炉子下面的液体包。四眼抢了他一步,用汗巾包住了炉子一摔,大量的酒精直接被汗巾吸收进去。我抓起汗巾按在王少胳膊上一阵猛擦,酒精所到之处,绿霉立马挥发殆尽,燃起一层层诡异的蓝色烟雾。王少龇牙咧嘴不住地喊疼,想要挣脱。秃瓢上来死死地扣住了他的肩膀叫我快擦。随着酒精一遍一遍地擦拭,蓝烟不断地从王少手臂上冒出来,铜钱般大小的绿霉很快就被我擦了个干净。
“我肏,姓胡的。你想杀人啊!”王少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自己的手臂疼得咬牙切齿。我见他虽然疼,但是整个人并无大碍,所以也就不计较这个小兔崽子出言不敬的事了。因为酒精反复冲洗的关系,被他抓挠过的皮肤起了一道道血印,又红又肿十分骇人。恐怕再晚几分钟,整条胳膊都要被他抓毛挂烂。
我心有余悸地拿枪杆子挑起尸茧外边的裹尸布,上面长满了寸把长的绿毛。面具酋长吓得瘫软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嚷着要离开这里。秃瓢说:“这玩意儿就算没什么危险,看着也挺碍眼的。不如一把火烧了它。”
王少嚷嚷道:“谁说这东西不危险,你看看我的胳膊!”
胖子挺惋惜:“好不好都是一件古物,带回去说不定博物馆还愿意出大价钱来收。烧了是不是有些可惜。”
我说:“你那点儿财迷心思还是等到下了百鬼坑再说,你看这周围百十具尸茧,只有东北角里的长毛了,地底下必然有古怪,你硬要带着生霉的裹尸毯下地谁知道会遇上点儿什么。”
胖子说此言有理,既然如此还是烧了为妙。我让他们把生有绿斑的裹尸毯带到角落里去烧毁,又走到被搬空的西北角看了看,只见空地偏右贴着墙壁的地方,平白生出一块绿斑,像一块幽绿的草坪横生在地表,面积不大,总共三尺开外的样子。
“你们看,这块地已经生满了霉斑,恐怕是地底下有不干净的东西在往上冒。如果不是这些尸茧年复一年盘踞此地、吸收绿霉,恐怕整片山窟都要被它们腐蚀干净。老巫医的记载果然没有错,巫医墓下面压着东西。”
胖子和秃瓢都是行动派,两人挥起铲子将地表上的霉菌铲起丢在一边,四眼说:“酒精可以消毒,也能用做照明,不能再浪费在这些绿霉上了。咱们往下挖挖看,实在没有办法再用酒精消毒。”
我扛起工兵铲和大家一同朝地下打洞,面具酋长跪在克瑞莫巫医的尸茧前,唱起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歌谣。秃瓢说:“这是野人们祭奠祖先时唱的哀曲,酋长可能是内疚,觉得自己引狼入室坏了先人风水。”
胖子不屑道:“这谁是狼谁是羊还不知道呢!你看老巫医本子里画的图,又是吃人又是剥皮的,如果不是咱们摸金的同行来得早,把这些克瑞莫野人驯化了一番,指不定咱们现在已经被这个老红毛烤来下肚了。快挖快挖,挖通了独角天神的墓,咱们也好替老前辈们出口恶气。”
别看马里克巢穴寸草不生,枯石遍地。这都是清末摸金人使的风水秘术,变换了此地的自然外貌,不过换皮不换芯,拨开葬窟中的碎石地之后,下面肥沃的土壤顿时跳入我们眼眶。这种红土松软厚实,十分适合植物生长,我们挖起来虽然费劲,但也好过在石头堆上打洞。因为葬窟内有足够的剩余空间,也不必担心有人来抓现成的。散土放风的工作就被我们略去了。五个人轮流打洞,轮流休息。整个作业时间不超过半个钟头,很快就打穿了一条通到百鬼坑的盗洞。
因为不确定底下的空气质量是否适合人类呼吸,我们戴上了防毒面具依次下到坑中。因为只有五只面具,自然就不能要求酋长与我们同行。王少怕他逃跑,说要用绳子将他捆起来,被我严令喝住:“他是个人,不是畜生。虽然心智尚未开化,也轮不到你这样折辱他。”
秃瓢说:“那打断他一条腿,省得多事。”
胖子“呸”了一声:“你们主仆二人少出这样的馊主意。他一没绳索,二没援兵。往哪里跑?天上啊!”
我说:“既然这样,那不如我冒个险,先戴面具下去,确定空气质量过关之后,你们再带他下来;如果不行,你们留一个人在上面看着他,这样万一底下出了纰漏,也好帮衬一下,不至于全部搭进去。”
胖子戴起防毒面具,朝我比划了一下,先一步跳进了盗洞。我急忙将面具罩了起来,紧跟着他跳了下去。L型手电好处在于轻便耐摔,所有零件都是塑料制成的,还有卡口,可以扣在口袋上。我将手电夹在胸前的口袋上,两手抓住秃瓢在上边拴好的麻绳“呲溜”一下到了底。胖子先我一步下洞,已经在地上插起了火把。两支火把一照,整个百鬼坑的构造跃然眼前。
“真是一模一样,老胡,你神了。”胖子见百鬼坑果然与上头的巫医墓一个格局,心悦诚服道,“要不怎么说知识就是力量,还是读书好啊,不读书怎么知道哪里有古墓,不知道哪里有古墓又怎么发家致富。”
“你当养猪呢,还发家致富。”隔着防毒面具,声音嗡嗡沉沉的,我举着火把照了一圈,对胖子说,“咱们可说好了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你少想念点儿那些明器。待会儿我先摘了面具,确定没问题,你就再去洞口放一枚冷光弹招呼他们下来。”
摘下面具之后,可视度明显有了改善。我深吸了几口空气,发现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见百鬼坑与巫医墓一样,是有通风口通向外面去的。我朝胖子竖了一个拇指,他点点头从包中抽出拔取式照明弹,朝着盗洞上方挥舞。我环视四周,发现这处坑洞不似人工挖掘,整个洞窟浑然一体,不见分室,更寻不着棺椁,漆黑的洞窟四壁是石质结构。用灯光一照,发现壁上纹有雕刻画。
“哎呦,这哪来的野草,扎人啊!”王少一落地,先是重心不稳,摔了一跤,他趴起来之后捂着手掌直喊疼。我说这坑百里无一物,别说草了,连蚂蚁都找不到半个。你磕着石头了吧?
“石头能扎人肉里面吗?哎呦,哎呦,疼啊!”王少甩了甩右手,不住地喊疼。四眼、酋长还有秃瓢也陆续跳了下来。
秃瓢一落地,急忙为他家少爷检查伤口,我凑过去,拿手电这么一照,只见王清正的右手心里插了一枚又细又长的尖刺。胖子说:“奇怪了,有人在这洞里啃过鸡骨头?”
四眼握住王少的手,用指尖挑了挑那个细刺:“不是鸡骨头,是人骨。”
秃瓢用大拇指按住伤口,然后轻轻一抽,将骨头剔了出来,他拿到光下照了半天:“这么细的骨头,怎么可能是人的。秦律师,你少吓唬我们。”
四眼白了他一眼,说:“是不是人骨,你们自己看地上。”
我进来的时间比他们都长,只顾着看石壁上的壁画,从未注意过脚下。经四眼一提醒,我们纷纷将视线投到地上。我之前一直以为脚下踩的是不平整的碎石。这时才发现,遍地铺满了白骨,碎得如同石渣儿。如果不是角落里还有些许未毁坏的尸骸,任谁都不敢相信,百鬼坑中所铺设的并非是白色的石英石,而是厚厚的人骨。我走上前去检查其中一具尚未碎裂的尸骨,这具尸体长手长脚,头骨有一般人的两倍大小,最不同寻常的要说头骨正中间的凸起,虽然已经被钝器磨得几乎不见,可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有一块骨质增生一样的东西长在额骨中央。“这里埋的,也是头上长角的克瑞莫巫医?”
“我看不像,”我提起一段腿骨在自己的小腿边上比画了一下,“你们看,长出了大半截,少说也有两三厘米的样子。”
王清正笑了笑:“怎么,就不许人家克瑞莫人比你胡爷高出一截?”
四眼说:“人体的骨骼是成比例生长的,就拿掌柜的来说,身高一米八出头的样子。那这些人骨直立起来以后,起码有三米的高度。”他一边说,一边又捡起一根骨头,“这不是个别现象,坑里的骨头随便挑一个起来,都是这样的骨骼比例。也就说,埋在这里的人,生前平均身高在三米左右。这和我们所见到的克瑞莫人完全不同,即使是自然环境引起的人种突变,也绝对不可能是短时间内发生的。所以这里埋的,必然与上头的群葬墓不同,不会是克瑞莫巫医的尸体。”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人种能达到平均三米以上的高度。”秃瓢用手比画了一下,“这太不可思议了。百鬼坑里埋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还是人吗?”
我想起老巫医的羊皮卷,清末的盗墓者是追寻着东印度洋公司的货船来到美洲大陆,他们最初要寻找的是深埋在丛林中的金脉。最后因为当地传说和得天独厚的地貌特征,断定马里克巢穴下面,有一处大墓。故而在异乡荒原干起了淘沙掘土的活计,不曾想祸从天降,挖出了一个葬满了“鬼怪”的妖窟,当初远渡重洋的换命汉子五人,只有两人从墓中脱逃。他们被困在丛林深处寻不着出路,最后更是一个个头上生出了鬼角,身上冒出了坑洞,成了妖窟中那些被埋葬的怪物模样。南洋生意人认为这是鬼怪作祟,对盗墓者发出的诅咒,于是又在妖窟上面平空建了一座“金鸡孵凤”,要破了此处的风水,断了百鬼坑中的煞气。他死后被剩下的幸存者埋在了风水墓中,用做震慑之能。再后来,因为生相变得怪异无法再融入文明社会,头顶鬼角的盗墓人索性留在了丛林中,与当地土著通婚,因为他特殊的样貌,和相对先进的科学知识,被土著们奉为圣贤,成了部落里的巫医。而巫医这一职能在盗墓者的子孙中代代相传,也不知道沿袭了多少代。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渐渐被遗忘,但盗墓者的后代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身上印着一个可怕的诅咒,所以才会在死前去到先辈们所建造的墓穴中坐化终了。因为只有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宿。
至于墓穴下方的百鬼坑,老巫医在羊皮卷中并没有详细地说明里面埋的到底是何方神圣,我想,一来是因为年代久远,老巫医也未必知晓前人具体见到些什么;二来,即使知道些什么,也未必会记录下来,可能是害怕子孙们擅自闯入百鬼坑,带来更大的灾祸。
只是我们眼前这些被剔去了鬼角的巨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何会被埋在这里,又有何异能,能在死后诅咒他人,使得一批盗墓者变成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怪异模样,从此有家归不得。我将寻找答案的希望,寄托在了岩窟上的石壁画上,就对王清正说:“王少你既然是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对墙壁上刻的石画是不是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王清正一路跟着我们,没少被揶揄欺负。一听我向他请教问题,眼睛笑得只剩一道缝:“好说好说啦,我王清正什么人,哈佛高材生哎!刘猛,上灯,让我好好研究一下这些壁画。”
我这样恭维他其实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很多人因为地下封闭,环境黑暗,会产生可视性幻觉,再加上百鬼坑中埋着独角巨人的遗骸,本身就极具威慑效应,让王清正解读墙上的壁画,给大伙讲讲历史自然好过一群人胡乱编造一些怪力乱神的小段子。我在各式古墓中,见过不少石碑壁画,但其中多是中式风格的散点透视画,墓室画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记录死者生平,第二种是描述死后的世界,当然也有第三种,那是单纯的祭祀用壁画,刻在墓中是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至于到底是为了防止墓主人死后被精怪骚扰,还是恐吓前来盗墓的摸金人,那就全凭后人揣测了。
王清正掏出小本子,边记录边解释说:“这面墙上的壁画,大致是讲述太阳神印提的子孙,战胜邪神,保卫家园的故事。这些壁画没有固定的时代顺序,需要做后期整理和排序。让我看看其他壁画的内容再说。”
面具酋长早就被先人留下的壁画吓得说不出话来,他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两掌朝上,面朝天顶行起了印加人的大礼。
胖子用胳膊肘偷偷顶了我一下,我跟他退到一边,他低声问我说:“他说的话可做不得准,我看这墙上的东西也没什么好研究的,选几块松散的,咱们装进背包,带出去换美元就是了。何必留在这里听他胡吹,找神庙和Shirley杨要紧。”
我说:“咱们进来都这么久了,你看你点的那两支老蜂蜡烧得正旺。考古和盗墓不同,他们更注重对历史的还原和解读,我们初到此地,对印加人的文化、历史都不熟悉,难得有这么一处古墓,里面藏着线索。多看一会也无妨,说不定能找到关于印加神庙位置的蛛丝马迹。”
胖子仰头,看了看我们身后的壁画,挠挠肚子说:“那老胡你看,这画上一大群人是在干吗,篝火晚会?”
我顺着他的视线望了过去,我们身后的这墙壁画又与王少整理的不同,用色鲜亮,我伸手摸了一下,大惊道:“是金粉!”所有人都被我的发现吸引了过来,四眼的眼镜都被吓得掉了下来,我们将所有的照明物都对准了我发现的壁画,在强烈的光照下,整面壁画折射出耀眼的金光,胖子几乎咬掉了舌头,高呼:“金子,金子做的墙。我的娘啊,这得值多少钱!”
这面壁画长六米、宽四米有余,上面印刻着一幅类似战争画面的历史长卷,我着实被眼前壮观的黄金画弄得紧张起来,再次凑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很肯定地说:“这不是纯金的墙面,只有石刻壁画的内容是用金粉涂抹上去的。这面壁画上的内容必然十分重要,否则作画的工匠不会这么重视,敢用金粉覆盖整幅壁画。”
金墙壁画一下子勾起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在金光的照射下,连角落里的蜡烛都闪耀出一股金灿灿的光芒。王少如获至宝,大声惊叹:“这张壁画太重要了,它是故事的核心部分,天啊,你们看,我们要找的东西都在画里!”
我盯着画卷仔细观察起来,画卷正中间,一个三眼长须的巨人浑身闪着金光,一手持斧、一手持杖,他双臂朝天沐浴在湖水中,身后跟随着无数印第安人,在他面前跪着一排排头上长角的长脚怪物。画卷另一端展现的是三眼长须人带领印第安战士将鬼角怪人埋入巨坑的场景。长须人脸上的三眼面具我十分熟悉,正是被竹竿子的人从国家博物馆盗走的印加公主面具。
秃瓢长期跟在王浦元身边,对该研究的东西早就了然于心,印加帝国的历史,他记得比谁都牢。“印加人在新王登基的时候,会用金粉将其包裹成一个金人,然后随同大量的金器一同浸入圣湖中,新王要在湖中沐浴洗尽身上的金粉,象征着将宝贵的财富献给了太阳神,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大致是因为印加人的创世神话中,两位开国的神子曼科·卡帕克及其妻玛玛·奥克略·瓦科二人都是从圣湖的的喀喀湖上岸来到人间。所以印加人坚信,水是沟通人间与太阳神宫殿之间的媒介。”
我说:“你的意思是,在当时拥有如此大的财力粉刷金墙,又对太阳神无比崇拜的国家,只有印加帝国。金壁上记载的是印加人战胜独角怪人的历史?”
王清正看得如痴如醉,他继续解读道:“他们战胜的不是独角怪人,而是天神。最上面的一组壁画,刻有云纹和太阳神的圆盘标志,这些独角人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传授印加人种植技术和天文知识。这里,你们看这里刻着一座镶嵌着太阳圆盘的建筑,有一个带着皇冠的长须男人在建筑前受到了太阳神的启示,要消灭独角天神。大家注意他的表情,瞪着眼睛、张着嘴巴明显是受到了惊吓。但是在下一组故事里面,一张黄金打造的三眼面具从天而降,长须人带上面具之后,手中就多了金斧和金杖,从此获得了神力。随即这位被赋予了神权的印加之王就拥有了消灭独角天神的能力,在他的带领下,印加人勇猛杀敌,将独角人的长角锯断,然后敲断了他们的骨头,活埋于此。这座坟墓是独角天神的衰落史,也是印加帝国走向繁荣的第一步。”
壁画上面触目惊心的内容,记录了整个独角天神被屠杀的全过程,虽然都是简单的石壁雕刻画,但是独角天神被断角凌迟的画面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特别是他们集体面朝天空发出嘶吼、挣扎时候的一组壁画,看得人简直仿佛身临其境,亲耳听见了他们凄凉的哀嚎。看完这些壁画,不难理解“百鬼坑”这个名字的由来,堆砌掩埋在这个地下洞穴中的,都是当年遭到屠杀的独角天神一族,当时的统治者害怕拥有先进科技知识的天神夺取他们的权利,所以在表面上假意奉承,实际上却是暗藏杀机,乘着天神眠息的时候,将其灭族。壁画中有一个头戴金冠的巨人,带着三眼黄金面具、一手持金斧、一手持金杖,他脚下踩着堆积如山的独角人头,宣告了在千百年前的那场战争中,王权对神权的彻底胜利。
酋长恨不得贴在墙上,可他心中充满了畏惧,只是指了指面具,用手在脸上一遮一掩,随后又指着金杖,不断地比画着插入地面的动作。秃瓢翻译说:“他说当初那个黄皮肤的人就是用三眼面具向巫医换走了向部落里的金杖。后来巫医死在了我们的枪下,他就生了贼心,将面具和金斧纳为己有,自封为神王一体的‘欧拉崩’。他现在追悔莫及,求我们将他留下,让他在洞中忏悔赎罪,度过余年。”
我对酋长说:“你这样消极避世不是长久之计,面对困难我们要勇于迎头赶上。在咱们中国,有一个和你们的印加王,那个“欧拉崩”一样伟大的领导人,他教导我们,不要害怕错误,敢于改正错误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你应当打起精神与我们一起去把祖辈们留下的宝物夺回来。你看壁画上刻得多明白,等有了面具、金斧和金杖,你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人了,到时候何愁不能带着乡亲们发家致富,走出雨林。”秃瓢把我的话翻译了一遍,面具酋长显然很心动,对我不住地点头。
王清正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壁画上的内容,胖子笑他充斯文。四眼为他辩护道:“王少这可不是装的,科班出身的人,非你我所能想象,他们对考古文物的兴趣远远超出常人。”
胖子说:“照你的说法,依我对明器的热爱程度来看,岂不是教授级别的人啦?”
我说:“你爱的那是财,关明器屁事。”
“非也,我王某人爱财不假,更爱闪闪的红旗,你给再多的票子也换不起我那一颗火热的红心。”胖子一脚踩在骷髅堆上,比画了一个冲锋上阵的姿势。我分析说:“现在可以肯定,这是一处早期的印加墓。我们要找的神庙应该就是壁画上的那座。”这一发现对于我们来说十分之重要,一来它证明了印加神庙的确存在;二来,它更正了我们一直以来的错误概念,包括王浦仁在内,我们大家一直认为亚马孙丛林中太阳神庙是印加帝国后期,退守二线时建造的。从壁画上的内容看来,太阳神庙早就存在于世,不过是印加人在后来的迁徙与发展中渐渐将其遗忘,直到西班牙殖民的闯入,使得帝国破裂,当时的国王这才想起了祖先们在丛林中留下的最后一块土地,于是举国迁往。难怪当年莉莉娅公主在落难之时都不忘从废墟中抢救三眼面具,那是他们印加国王权的象征,从太阳神那里得来的天赐之物。
我至今不能理解的事有两件。第一,莉莉娅公主与格林教授结成夫妻之后,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前去中国,最后又被人发现冻死在安第斯山脉的冰藏区内;二是壁画中金杖的作用,竹竿子费劲心机从博物馆盗取面具,难道只是为了与酋长交换金杖?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根金杖在寻找神庙的过程中必然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是我们这队人所不知道的。想到这里,我不禁头疼起来,总觉得有一些关键部分被遗忘掉了,怎么也想不起来。
秃瓢接话道:“既然黄金面具的谜题已经解开,我们也该是时候上路了。这地方毕竟是个坟场子,待久了未必是好事儿。”
王清正还想读完全部的壁画内容,他一反大少脾气,此刻用小本子认真地做上了记录。我对他说既然百鬼坑已经被我们发掘出来,日后你们王家想怎么勘察研究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何必急于现在。前面还有印加神庙在等着我们,失了老祖宗的霸王印你可担待不起。
王少正在兴头,谁拉也不走,挥了挥手说:“有种的拉我一下试试,老子偏就不走。”话音未落,墙角的火把和蜡烛忽然“扑”地一声同时灭了个干净。黑暗中,不知道谁的牙齿在咯咯地打着颤。